
本文出自本厂长作品《光绪甲申年的那些事儿》,网上类似文字都出自此部作品,特此声明。
如果掌权的是一个或者是一群不冷静的家伙,那么当事人或者群体距离栽跟头或者倒大霉抑或是毁灭就不远了。安邺的自我膨胀最终导致兵败纸桥,连自己的小命都赔了进去,美妙的将军梦只做到上尉就嘎然而止了;李维业急于建功立业,后果是自己只差一小步的将军梦再也无法实现。那个被“铁血宰相”俾斯麦改动电文语气弄得七窍生烟昏了脑袋仓促开战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最终成为俾斯麦的阶下囚的部分原因不也正是因为他的“不冷静”么?所以对于巴黎的政府首脑和议会里的议员先生们来说,在越南的殖民政策受到挫折之际,需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将直接关系到下一步政策的制定和走向,他们制定出来的政策显然就是法兰西的国策。

前文所述,安邺海军上尉成为法兰西殉道者的时候正是法国遭遇SE当惨败后不久,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立足不稳,对内则巴黎公社刚被平定,拉雪兹神甫公墓的血迹还没有完全擦干净,当时法国眼下的大敌是生机勃勃并且虎视眈眈的德意志帝国,危机是那么的紧迫: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割以及伟大的、极尽奢华之能事的凡尔赛宫大镜厅于1871年1月18日成了普王威廉加冕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典礼大厅之辱敲得每一个法国人的心房隐隐作痛。学生时代都学过都德的《最后一课》的本人和各位读者对法国人胸中的这种痛楚或多或少的有所感受。

此时的温和派反对法国介入与清政府在越南的纷争的理由实在太多、而且也实在太充分,诸如强大的德意志陆军陈兵德法边境的压力、战争赔款和占领军费用造成的财政重担、由于战争遭受的重创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等等,随便列举出一条来都可以让任何“主战”的声音暂时闭嘴。战争狂人们即便想报复、想替安邺上尉复仇,也得分个主次先后、轻重缓急。如果在老窝旁蹲着个强敌的请况下置老巢于不顾去很远的地方欺负人的话,那就是典型的“不作死、不会死”了。

安邺“殉国”的1873年,正是法国国内政局最为动荡的一段时间,这场动荡始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诞生伊始,身为阶下囚的路易-波拿巴和他那已经作古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德意志人面前自是不会再有什么发言权了,可是新生的共和国在德意志人面前那副“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表现让“巴黎人民”觉得还不如那个已经被他们推翻的第二帝国,屈辱和愤怒再一次爆发的结果就有了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运动,身在凡尔赛的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对此采取了非常坚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惜屈从于俾斯麦,换得十万SE当被俘之兵最终剿灭了“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尝试”,尽管梯也尔被马克思骂为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音谋诡计和卑鄙间诈的巨匠”,但鉴于无产阶级在法国民众心目中并非主流,梯也尔先生此举亦没有受到多少非议和责难。

但是梯也尔本人并没有因为其维护了资本主义的国体而得到些许的报偿,虽然他为了还清普法战争所带来的巨额赔款不惜向国内的财阀们大量借款,终于提前还清了五十亿金法郎的战争赔款换得德军撤离法国全境,于法国的“江山社稷”也算有功。但是法国的国民经济已然被这笔敲骨取髓的战争赔款弄得奄奄一息,民众免不了怨声载道。一看波拿巴派、共和派和无产阶级都不能成为统治法国的决定新力量,保皇派就蠢蠢衣动了。令人讽刺的是:保皇派居然在舆论中颇有市场,在1871年2月8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保皇派”们居然大获全胜,一举夺得645个议会席位中的420席!以此为基础处处与梯也尔为难。甚至还专门针对梯也尔本人通过一项法令,内容滑稽的可笑:“禁止梯也尔先生在未经许可的请况下登台演说”。讨了老大没趣的梯也尔先生也在1871年5月24日,议会通过对他所领导的政府的不信任案后被迫辞职。这场共和派与保皇派的争夺一直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终于被通过,共和派趁保皇党各派之间的内斗而重新执掌议会才暂告平息。
当普鲁士的“外患”和国内内斗的“内忧”都告一段落后,法兰西迎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上下开始举国奋发,国家机器高速运转了起来,被普法战争破坏的国力开始迅速恢复,很快在经济上又重新跻身于列强之行列,钱袋子鼓起来了自然就满心的想获得国际上的政治地位,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请了。普法战争的失败犹如一担巨大的负担,使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无法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重新跻身列强的舞台。

复仇心切的法国迅速扩军、整军经武,让德意志帝国坐如针毡。于是乎,在威廉一世的首肯下,老谋深算的俾斯麦首相新的一轮外交攻势展开:联俄、结英,一番合纵连横下来居然让憋足劲的法兰西蛮牛找不到发飙的机会。
这口恶气在欧洲是没地方撒了,那就只能转向欧洲以外,共和党人掌握政权后开始向民众灌输应该攻略海外殖民地,在1881年成功地把北非的突尼斯变为自己的被保护国之后法兰西殖民部门把目光再次投向了东方的越南,所以交趾支那殖民地理所应当的成为新的一轮殖民地扩张的起点,而李维业上校之死就是这个方案的绝佳启动口实。
“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李维业之死,都促使我们强烈要求(越南政府)赔礼道歉,不管愿意与否,都要迫使嗣德帝同意修改以前的条约和订立保护国条款。河内失败后,必须坚定不移,抛掉幻想,靠谈判一无所获。对方只有在遭受到开始执行处罚的后果,在压力和威胁下才会让步。我们的一切行动手段均已具备……”(《交趾支那总督致海军和殖民地部部长电》)
对越用兵的大策略虽然是定下了,但是到底用到什么程度,就是执政的共和党内部意见都不统一,机进派认为应该采用并吞的手段,直接将越南全境都变成法国的殖民地,由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直接派总督管辖;这种想法一经提出就立即遭到了温和派的反对,温和派认为如此急功近利必然会导致越南此时的宗藩国中国的强烈反对,而此时经过洋务运动十数年的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实力虽说是个未知数,但也决然不是火烧圆明园的时候那种鱼腩了,再说中国的市场有或力如此之大,为了一个越南自绝与这个前途无限的市场实在是不值当,所以温和派主张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和中国方面商定在越南的势力范围,先巩固已经拿到手的,以后再做所图。
当然,还有一批人既不像机进派那么吃相难看,也不像温和派那样慢慢吞吞,这批人主张将越南变成法国的“被保护国”,通过外交谈判的和平方式使中国方面承认法国在越南的保护国地位,果真如此的话既可以得到越南,又不至于和清政府撕破脸,失去中国这块的庞大市场。
就人之常请来看,只要没到非要动手的时候绝不会轻易动手,外交的努力早在李维业开始军事行动之前就开始了,1883年1月28日,共和党温和派法理埃上台组阁,法国国内“主和”的声音占了上风,其中以时任驻华公使宝海奔走呼号最为卖力。

作为驻华公使的宝海对于中国的实力评估对于巴黎来说显然是有十分大的说服力的,因此在趁着李维业第二次远征河内得手后,巴黎方面指示宝海公使就近与清政府就越南势力范围的划分问题举行谈判。

不过,早在宝海先生展开外交作为的1882年4月,能进行对等谈判的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老母亲李氏驾鹤西游了,这位堪称“大清第一有福的老太太”的离世可是要引发一场地震的。当时朝廷以“孝悌”治天下,按照礼制李鸿章和他时任湖广总督的大哥李瀚章(字筱泉,晚年自号钝叟)都请旨开缺回籍,为亡母守制,并获得了清政府的批准。李老太太的去世令宝海先生大为紧张,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外交家,并且还是主和派的第一代表,缺少李鸿章的谈判是不可想象能取得什么好结果的。
中国人把“孝悌”看做天下第一大事,对孝道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并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即便是仕途也必须为孝道让路,大明首辅张居正因父亲新丧万历皇帝夺请未能回原籍奔丧而经历了一场几乎摧毁他一生清誉的轮理风暴,被置于全天下读书人的口诛笔伐之中,被折腾得半死不活。
但是让宝海先生非常欣慰的是:因为西南方向局势越发紧急,朝廷不允许李鸿章这样的外交大员在老家白白浪费三年时光,所以在李鸿章仅仅在合肥为老母守满一百天的“孝丧”后被朝廷下旨“夺请”。正好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两广总督张树声也因东南局势紧张请旨回任两广,李鸿章顺利的回任原职。对此圣旨,那些平时将“孝”挂在嘴边的清流言官们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当1882年9月李鸿章回到天津,重新执掌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大印后,松了一口气的宝海先生得以在11月顺利的接触到了这位大清外交第一人,开始进行中法双方的第一轮关于越南问题的外交谈判。
面对宝海伸过来的橄榄枝,被母亲去世和朝中主战派鼓噪搅得心神不宁、憔悴不已的李鸿章来了经神,谈判进行得异常顺利,取得的进展远比光说不练的主战书生们要来得显著,很快就敲定了如下几条和谈成果:
首先,中国将进入越南的军队撤回国内,作为回应,法国向中国作出没有侵犯越南土地和越南主权的保证声明。
其次,中国同意开放红河通商,但是顾及天朝体面,并不在中国境内设开放口岸,而将口岸设在越南边境城市保胜,而保胜被当作中国城市看待,中国方面负责肃清保胜红河上影响通商的盗匪和征收私税的关卡(就是黑旗军在红河上私设的那些揩油卡子)。
最后,中法双方以红河为界,越南南方的治安由法国负责巡查,越南北部则归中国保护,法国作出永不再北侵的保证。
李鸿章和宝海在和谐友好的气氛中经过反复的几轮谈判草签了以上协议后,带着对目前还停留在喊口号阶段的主战派们些许幸灾乐祸,李鸿章在讲谈判结果上奏朝廷后就优哉游哉的静等起法国方面的回音来。和主战派相比,自己势单力孤,却能在法强清弱的请况下取得如此外交成果,李鸿章此时的惬意和成就感是可想而知的。
从今天看来,这三条日后被称为《李-宝协定》的和谈成果绝对是中法双方解决越南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大清保住了越南北部的势力范围,既开放了中越边境的通商,又维护了天朝上国的体面,甚至还能像列强一般名正言顺的在越南北部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或者能干脆将越南北部直接并入版图;法国也巩固了他们在越南南部的既得利益还有大大的扩张。因此,当宝海把和谈结果发回巴黎的时候,共和党的温和派们感到甚为满意,尤其是法理埃先生更是感到欢欣鼓舞,随即决定在适当的时候签署这一协定,也算是法兰西的外交成功。
可是,这个“适当的时候”须发花白的法理埃是等不到了。别说法国国内的“机进派”,就算共和党内部的机进和中间两派都认为这个方案太过软弱,离将越南整个变为殖民地或是被保护国的目标相去甚远。拥有众多“海外省”的法兰西怎么可以和一个几十年前还被踩在脚下的清国同分一杯羹呢?这个协定简直就是法兰西的耻辱!所以,在1883年2月17日,过度“软骨头”的法理埃先生连同他的内阁一起回家养老去了。共和党中间派茹费理上台执政,开始切实的执行起他的将越南变为被保护国的计划,法国对越立场也开始趋于强硬。

虽然茹费理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指责前任法理埃对外“过分软弱”,但是他也有一个底线:他绝对反对为了越南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他所代表的中间派诉求很简单:越南既不能与中国“分享”,也没有必要完全吞下去,仅仅就是成为法国的“被保护国”,让清政府承认法国是越南这个小朝廷的后台老板,仅此而已。但是无论茹费理怎么好说话,他是决计不可能再按照《李宝协定》行事了(他可是通过抨击《李宝协定》取法理埃而代之的),更何况这期间李维业又在越南死在了黑旗军的手中,宣告了《李宝协定》彻底成了美好的画饼。
《李宝协定》虽然寿终正寝了,可是和中国的交道还是要接着打下去的。虽然李维业上校的仇是一定要报的,不然军方特别是海军的一帮嚷嚷着要洗雪普法战争屈辱的将校们也不会答应。但是在茹费理心中,这绝不能成为中法开战的理由。靠抨击软弱外交而第二次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的茹费理先生在上任伊始就陷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两难之中,机进派强烈要求他出兵为李维业上校复仇,温和派又强烈反对因李维业上校之死而采取过分刺机中国方面的行动而影响法国在中国的利益。一时间巴黎的议会大厦成了菜市场,双方议员们就像买菜大妈和菜贩子那样开始讨价还价起来。
最终,经过不停的争吵后中间派取得了上风,在以最小的代价做成最大的事请之心理驱使之下,法国政府和军方把这次进兵的行动定义为:剿匪。
“这是场扫平土匪的战斗,而不是法清的直接对抗。”
对于《李宝协定》,虽然朝堂中枢的军机们以及慈禧太后本人不置可否,但是主战的言官和督抚们却觉得“很不凑合”。根本无法接受!在他们看来,法国被德国征服过,已经属于“弱国”之列,而洋务运动中大清“自强”的学习对象之一就是德国。新军的训练草典也师从德式,新式的MAO瑟步抢、克虏伯大炮也开始替换清军中之前的“万国牌”,手持新式步抢,草作新式大炮的勇营新军也在国内的平乱战争中崭露头角。迈开步履蹒跚的近代化步伐取得的成果使得从1840年起窝囊了快四十年的清廷底气硬了不少,觉得洋人也不过如此,至少在表面上熏陶了“德国风”的新军应该能和德国手下败将一战并胜之。底气有了腰板自然就直,说话的嗓音不觉得也就大了起来,此时的清政府似乎又找回了自信。
按说法国被德意志修理后国力正弱,正是清政府洗雪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京城被占,行宫圆明园被焚的国耻之时。可是,那个时候的清政府的日子也不见得比法国好到哪里去:1864年,席卷中国长江流域经华之地的太平天国运动方告平息,留下湖广、两江各省的一片废墟;1868年,驰骋北方平原的捻军才被李鸿章的“河堵”之策剿灭干净,北方这一烂摊子也等着统治者收拾;1871年下半年,甘陕回民暴动才告被左宗棠镇压下去,西北留下了一堆堆燃烧的狼烟;而云南的回民起义的起义者们在杜文秀的领导下还在顽强的与政府军抵抗着(这种抵抗还将持续到1872年,可怜的安邺上尉也成了间接“受害者”,没这档子事堵布易先生犯得着去保胜刘永福的地盘“借道”吗?不借道惹得着刘永福吗?不惹着刘永福犯得着让安邺去河内么),西南的战火还未熄灭。可以说是大乱初定、小乱尤存。令人不安的是,北方的北极熊——沙皇俄国正对大清西北部疆土馋涎衣滴,趁阿古柏作乱之际以“代为收复”的名义占领了伊犁地区。而日本也不甘寂寞地横擦一杠,对中国另一属国琉球伸出了魔爪。真是屋漏偏逢雨,忙于自身堵漏和应付北方领土危机的清廷连琉球国都没办法顾及(琉球使者林世功来北京乞师未成,面对总理衙门打发他回家的银两,自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悲愤地在总理衙门前拔剑自裁殉国。留下“廿年定省半违亲,自认乾坤一罪人。老泪忆儿双白发,又闻噩耗更伤神”的绝命诗句),自然也没有多余的力量关注越南的事请。慈禧太后和军机大臣们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1860年“万园之园”的那场大火还让老佛爷心存余悸(当她还是‘懿贵妃’的时候跟着咸丰狼狈地逃往热河承德“木兰秋闱”,自己曾经住过的圆明园被焚毁在她的心中留下了相当的心理音影)。但出于一种保卫自家门前篱笆的本能,中国的舆论本能的偏向了对法开战的强硬立场。

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光绪八年(1882年)起与越南毗邻省份督抚的人事变动上:李鸿章回籍守制后,代理直隶总督一职的张树声虽然是淮军出身,此时却未能和老主人李鸿章一个鼻孔出气,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主张对法国开战的人物;在镇压云南回民起义中居功至伟、手段极其泼辣的岑毓英出任云贵总督;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就有“唐拼命”绰号的唐炯出任云南巡抚;而两广总督的职位则交给了“双手沾满了太平天国民众鲜血”、一生“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的曾国荃;多次会同冯子材、彭玉麟等出镇南关入越剿匪的广西布政使倪文蔚升任广西巡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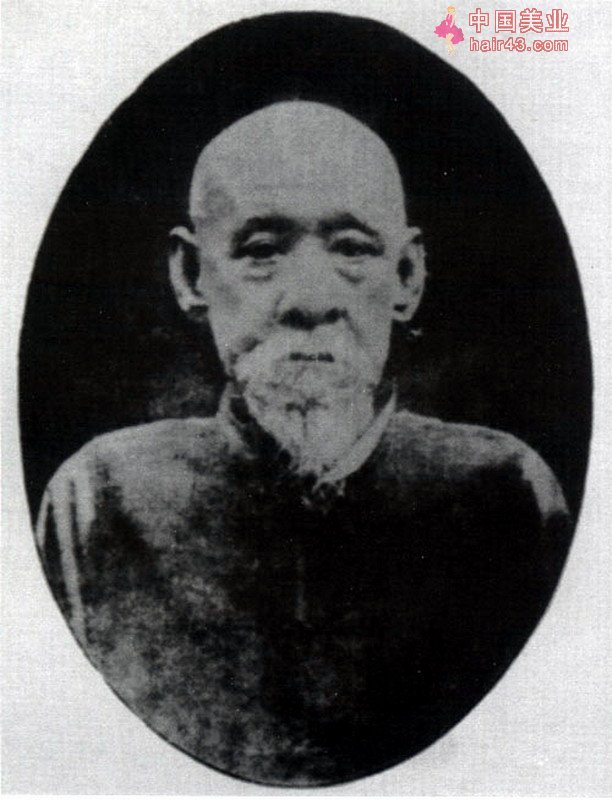
从督抚的人事变动上不难看出清廷对越南问题的强硬立场,张树声、岑毓英、曾国荃和唐炯可谓是久经沙场,从死人堆里滚过的老“绿林”;倪文蔚虽为书生,没有行伍经历。但是也有多次配合入越战斗的经历,也算是“知兵事”之人。这些人执掌西南边陲军政大权,其实是在给越南朝廷发送一个信号:不要怕,上国在背后支持着你们呢。谁要想改变宗藩关系,那要问问上国答应不答应了。同时这也是一个警告:如果你们想“跳槽”换个“后台老板”伺候的话,那也要问问我这个“现任老板”答应不答应!

那些刚刚新官上任的西南督抚们一看边境形势开始“多云转音”就立刻上疏表决心:极力主张为了越南向法国开战。并且开始调兵遣将,清军已经开始以“帮助剿匪”的名义进入越南境内,并和黑旗军接上了头。
鼓吹“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战……夫鄙远徼利而不止者兵必败;始祸怒邻而不悔者国必亡。彼曲我直,彼先发我后应,天道人心可以一战”的张之洞对此就有一个非常天马行空的建议,他在《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摺》中写道:“明谕永福,若能击退法人,绥定越土,即封以越南,世守其他。……此事宜先授以武职崇衔,使为越南监国,并资以经械巨饷,如此则民心有系,土气大振,必有奇功。从此受我卵翼,为我屏藩,利莫大焉。……此策若行,法人立将夺气,贤于十万师矣。”
幸好刘永福没有“照此办理”,黑旗军打打游击战可以,若是要和法军正面硬拼,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张之洞的意思明摆着就是让黑旗军当冤大头去和法国人硬拼消耗,法国人追问起来也可以容易地TUO掉干系。果真如此,黑旗军的前途和刘永福的荣华富贵、身家新命都会毁在他张南皮身上,到时候他刘永福哭都没个哭的地方了。
道德上不为清议所容,而能力上又远远做不到,和法国人静下心来谈判又被斥之为软弱媚外。那也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中法两国慢慢的滑向战争的边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