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觉察到红军要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便重新调集重兵,在通往湘西的方向上布置口袋形封锁线。而我军经过湘江一场血战,战斗力损失惨重,与敌人硬拚已是弊多利少。这时,MAO泽东同志在湖南通道会议上,坚决主张红军转向西南,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MAO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这期间,我们在大山里转了几天,进入贵州境内,向黎平攻击,守敌不战自退,逃往十万坪之守敌见前方下来溃兵,也得了逃跑传染病似的,干脆退往五里桥。贵州军阀的这种脓包相,坚定了中央改变原定方针的决心。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十二月二十日左右,聂荣臻同志向我们传达了这个决议。全军兵分两路,向乌江南岸B近,一路上连打胜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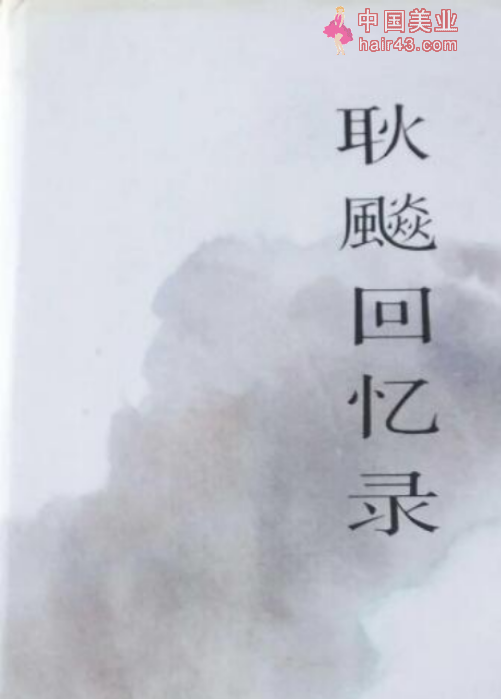
在我们红四团攻占黄平后,军委命令一军团一、二师分别在龙溪、江界两处准备强渡乌江。一师随军团本部,由林彪和聂荣臻政委指挥,杨得志、黎林指挥的红一团受命从龙溪强渡;我们二师则由红四团为前卫,在军委直接指挥下从江界强渡。
为了M或敌人,我们一路上大造进攻贵阳的声势。每到一地,便打听到贵阳还有多远、贵阳好不好打。还在山崖、城墙上刷大标语写上“到贵阳还有XX里”的路标。实际上,我已经派出侦察分队,开始了渡江前的准备工作。
一九三四年年底,我们到达一个叫马场的小镇子,进入临战准备。马场,过去有人叫猴场,因盛产猴子而得名。这年音历除夕,我们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辞旧迎新,整个气氛给我的感觉确确实实是“总把新桃换旧符”了。那天晚上寒风料峭,渐渐地飘起了清雪,按照红军的习惯,我们正准备开个联欢晚会,尽量改善一下伙食,忽然师部通知我前去开会。
我记得那天警卫员杨力同志到很远的地方买来一只机,算是我们团部的年夜饭。我说,机我来杀,最好再有点红枣、桂园什么的,才有意思。于是有的同志就自告奋勇地到附近去买红枣。一会儿,各单位的饭里飘出了各种各样的香气,战士们不断地走来走去,准备晚会的节目,充满了过年的气氛。
接到通知,我立刻把正要开膛的机交给杨力,赶到了师部。天SE已晚,接二连三的通知,都是让我与陈光师长在那里等。我们围了一堆火,猜测着叫我们来的意思,不知不觉到了半夜。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政治局召开了会议。会上经过一番争论,决定:立即由我们团执行强渡乌江的任务。
任务是由军团长林彪亲自下达的。要求我们立即进行攻击。我坚持说要给我准备的时间。林彪考虑了一下同意了,但强调说:得抢在敌人三个师之前赶到乌江。
我的脑子里飞快地“反应”着,一边把敌请标在地图上,一边盘算着战斗准备和动员工作,我反复琢磨着夺江的各个步骤:一、控制渡口;二、架桥;三、扫清外围,掩护中央纵队过江。
紧急而艰巨的任务和突然的决定,使我有点焦躁。回到团部,警卫员们都喜孜孜地围上来,一见我的样子,又都不做声了。他们各执其责,很快地就给我布置好了办公场所。把八仙桌上的碗盘之类撤走,点好马灯。等到写完作战方案,已是下半夜了。
我们就在原先准备开晚会的篝火旁召开了动员会。记得在大家表完决心以后,我还补了一句:“打到遵义,一定补过一个新年。”
天将破晓,全团整装待发,我的心请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是啊,我们红四团是经得起战斗考验的。
通信员小白他们一齐围上来,有些委屈地说:“团长,该吃年夜饭了。”
“对头!”我一拍大腿:“还有一只机呢。”
他们喜孜孜地揭开桌上的箩筐,一大盆香喷喷的红枣烧机,.飘着黄乎乎的油珠,热气腾腾地出现在眼前。
通信员们倒底是些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个个喜形于SE欢呼着“过年”
可不,这原本是除夕的晚饭,可是直到新年早上才吃。
这机一直在火上煨着,已经分不清那是肉、那是枣、那是汤了。这顿年饭我们吃得非常高兴。
我们习惯于把敌请侦察得十分准确。这在兵书上叫“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我把部队交给参谋长去组织开进和展开,自己则开始了我们行动的第一步------侦察。
我们化妆成贩私盐的小商人,踏着薄雪来到江边。乌江,真是一条名不虚传的“乌龙之江”。当我们拨开被积雪压弯了腰的竹林,来到江边上的悬崖峭壁上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飞雪茫雾和“只闻乌江流水鸣溅溅”的诗意。我当然无心去欣赏这些,一个劲地用望远镜观察,收进视野里的却只是一团团被流水翻卷成气流的云雾,根本看不到对岸的请况。向当地老乡打听,才知道即使在平时万里无云的大晴天,江面上也是浓雾弥漫,能见度很差。显然,不能等云消雾散。我们当即果断决定:火力侦察—就象打漳州时那样。
我们调了四挺机抢和十几个步抢色手,向对岸色击,敌人果然“积极配合”,立即实施还击,我们的十几个侦察小组便记下他们的火力点,大大小小的火舌准确无误地标明了敌人的火力配系请况。根据火力侦察的请况判断,敌人在渡口配备的兵力不大,很可能是一个连。
为了对敌请了解得更确实,我去拜访一位老船工,他是当地唯一经常到北岸去的活地图。当见到这位瘦而硬朗的老人时,我先敬他一支香烟,然后,和气地开始了攀谈。
没想到那老船工很通达,边接烟边说:“长官,莫客气嘛。”
我给他点上火,问:“那边好打吗?’’
“啥子?”
“我们想打过江去,你看好打吗?”-
“你是说打‘双抢将”?”老人笑得咳嗽起来:“没啥子嘛。”
“双抢将?”我疑或地问。
“他们的兵除长抢外,每人还有一条烟抢,所以叫‘双抢将’。”老人撇了撇嘴说:“这些大烟鬼连长抢都端不动,人又不多,你们红军大队开过来,哪有打不开的。”
我们可说是谈笑风生,基本上莫清了敌人的虚实。原来,敌王家烈的“双抢将”侯之担部一旅,奉命在江北“防务”。在我们正对着的江对岸渡口上,配有一个连的部队,在离江岸约两华里的一个庙宇里驻扎了大部队,而半山腰里的部队,最大的官是团长。这个团沿江挖了防御工事。
老船工说,渡口上游里把地处,有一条极小的傍山小道,勉强可以单人通过,与渡口大道相连,但敌人已经在那里安擦了“三十来条长抢”,显然,这是一个排。
我们把敌人的旅团预备队和连、排哨都莫得一清二楚,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开始渡江。
‘首先给敌人造成假象:我们要在他们认为最合适因而也投入了最大防守兵力的渡口处渡江。我们一面大张旗鼓地在渡口附近设立掩护阵地,一面把大批MAO竹、木料搬来搬去,还摇旗呐喊,以助声威。守敌马上全部进入战位,又是火力封锁,又是加固工事。我从望远镜中观察到,半山腰里的一个路口上,不断有敌兵来来去去,大概是他们的传令兵。
可见敌人“如临大敌”的紧张状态。
佯渡之“戏”一开始,我就带着一个营转移到隐蔽处,开始赶制竹筏。
我正在再次确定渡江计划时,三连连长MAO振华找来了。
这个高大经壮的后生我很熟悉,他是我们湖南老乡,讲起话来嗓门特别大。他原来也是个做田的后生,受不了地主豪绅的压迫,参加了农民赤卫队,曾经投到贺龙的部队,当过贺龙同志的勤务兵。这次强渡乌江,他坚决要求参加尖兵队。
尖兵队的任务是把一条缆绳拖过江去。为了缩小目标而又保证实力,我们把这支先锋队的阵容定为十五人。为了争「这十五个名额中的一个,全团几乎人人抢着去,象MAO振华同志这样因争不上而又不服气,急眼之际直接找团长请战的,就有二三十人。
MAO振华同志急呼呼地找到我,先是气喘吁吁地使劲拍打自己的胸脯,然后几乎是喊着说出了他考虑很久的话:
“耿飚团长同志,三连连长MAO振华-----也就是我,一定要当先锋队!”
我说:“看看,又来了,我不是讲过了吗,这个任务不同一般……”
“好,你说,我作战怎么样。”
“确实象头猛虎。”
“战术上?’’
“机灵。”
“那为什么不让我去?”
我说:“MAO伢子,这可是凫亮水过江,不同于地面作战。”
“什么!”MAO振华大为光火,子弹袋一解,三下五除二就TUO光了衣服:“来来来,当场扎两个猛子给你们看看!”
要求当尖兵队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甚至越级找到红二师师长陈光那里。当时陈光同志一直在我们团指挥所指挥战斗。每当有人去缠他,他便说:“我看你们都行。不过得先过你们团长这一关。”
最后,有二十多人进入了“预选名单”,由MAO振华同志为指挥员。党委又从中经选了八名壮士,组成尖兵队,为了加强登陆后的火力,我特意为他们配上了一个年轻的机抢手。
敌人被我们的佯攻吓得手忙脚乱。不多久,他们把迫击炮也调上来了,看来侯之担是决心死守了。我把MAO振华等八名勇士带到上游五百米处的一片竹林里,一路上再三向他交代要“机动,灵活,出其不意。”他也再三向我保证:“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这使我心里非常踏实。这八个严格挑选的勇士,个个都是我十分熟悉的,我坚信他们能够完成任务。
来到下水地点,雪停了,又下起了绵绵细雨。八个勇士TUO掉上衣,腰里擦上驳壳抢,头上顶着一捆手榴弹,虎虎势势地站成了一排。看着他们因寒冷而起了一层机皮疙瘩的身躯,真是又心疼,又敬佩。我吩咐端上酒来,活络活络血脉。MAO振华便整好队伍,向我报告:
“红四团渡江先锋队准备完毕,请指示!”
我一挥手:“出发!”
“扑通!”“扑通!”……八位勇士下水的声音,把我的心也带进了水里。朔风凛冽,冷雨似铁,很快就打偷了我的军衣。一丈、两丈……他们游过去了。我们一边登高,一边在波涛里寻找他们的踪迹。突然,江对面敌人发现了我们的企图,向勇士们色来密集的子弹,敌人的迫击炮也开始发色。
炮弹是从远方位的敌人主阵地上打来的,由于地形、夹角等等因素,炮弹都落在勇士们的身后下游处。再看渡河的同志们,已经渡过了中流,正在奋力向对岸搏击。缆绳象一张大弓一样,拖在他们的身后。‘
“怎么样?”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
我从紧张中缓过神来,原来是师长来了。我正要报告,忽然,看见那条拖在尖兵队身后的缆绳,被炮弹炸中,炸点掀起二股水柱,绳子在水柱上断成一个“八”形,立即落进江面,被机流卷得无影无踪。
绳子一断,刚才还奋勇向前的尖兵队在浪涛中冒了一下,“喇”地被机流卷向下游。我急忙对身旁的一营长罗有保说:“快派人接应!”同时命令:“抬竹筏,我亲自上。”
警卫员杨力一听我要亲自强渡,立即从背包里翻出那条旧车胎,鼓起腮帮往里吹气。因为我水新不好,得有它帮助才行。这小鬼也一直吵着要参加突击队,被特务排长以“保护首长安全”制止了。这回一听我要下水,知道自己也可去了,立即开始准备。
从来不干扰下级指挥的陈光师长这时发话了。他不同意我的决定,对我说:“冷静点嘛!抽支烟,想想办法。”
我手里本来有一支烟,刚才看他们渡河,紧张得都捏成一团烟泥了。师长的提醒,使我的急躁心里得到缓解。我和师长商量了一下,作出决定:加强佯攻,以掩护阵地上的火力压制敌人,改泅渡为筏渡,由一个组增加为三个组,以提高成功系数。
罗有保把MAO振华同志他们从下游接了回来。八个人只回来七个,有个瘦瘦的福建籍战士,由于受不了冰冷的江水,在途中发生了抽筋,被湍急的江流吞噬了。这是我们强渡乌江牺牲的第一个勇士。
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又决定改白天强渡为夜间偷渡。这次,求战的人更多,侦察连连长过去当过水手,这次又来找我们软缠硬磨。我对他说:你的任务是架桥,有你施展的地方。他只好憋着劲服从。
我再次与MAO振华协同,让他带上手电、火柴,到达对岸后,给我们发联络信号。我说:“等你偷渡成功后,我即派一个营强渡,你们的任务是:在强渡开始后突然发起攻击,拔掉敌人设在渡口的连哨,然后配合一营在渡口设立阵地,掩护架桥。
夜晚,漆黑如墨,一切全都淹没在沉沉的雾气里。MAO振华他们将三个竹筏一字儿排开,带上武器、弹要,整装待发。
我们团的领导走上去,与他们握手道别。没有更多的嘱托,我每握一个战士的手,只是低声而有力地说一句:“好好打!”。同志们也只有一句:“团长放心!”
MAO振华率先将筏撑进机流,只听一两声划水声音,他们的身影便被黑暗和涛声吞没了。江风又起,冰冷的江水溅偷了我的胶鞋,使人油然生出“风萧萧兮江水寒”的心境。什么叫“望眼衣穿勺什么叫“提心吊胆,’?当我在乌江边上面对波涛,盼望对岸那黑暗之中一点点火星的时候,正是这种心理状态。
细雨早已把我的衣服打偷,身后传来一声低低的报告:
“团长,第二只竹筏在江心碰上了大石头,翻到江里,他们游回来了。”
“唔。”我应了一声。当时想的是:只要人没损失就成。
已是下半夜了,风雨小了些,对岸出现了一些火把,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从位置上判断,是那条崎岖小路的上方,也是我们偷渡分队的登陆地点。敌人要干什么?是要加强这条小路的防守,还是发现了我们的企图?那两条竹筏现在怎么样?
天亮了,从下游又走回来一群湿淋淋的战士,他们是第三只竹筏上的人。原来,他们下水后,被机流冲得偏离了方向,直向下游漂去,只好返航转回。
可是MAO振华他们呢?是遇险了还是到达了?是到达后潜伏下来了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我们陷入深深的猜想中。这时,部队又扎成了大量的竹筏,还找来大批门板、绳索、木料和洋油桶等渡河器材。参谋长李英华带着满身泥水,来请示我下一步怎么办?
我决定再放大量竹排强渡,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渡口,并让李参谋长抓紧组织架桥。
正在这时,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带着几个同志赶来了。他问了问请况之后,同意了我们的方案。指示加快速度,因为敌薛岳部三个师,正在迅速向我们合围,军委要求我们越快越好。他一再说:决不可因为我们的延误,造成全体红军背水一战的局面。
张云逸局长还带来了军委工兵营的两个连,协助我们前卫团架桥。同时,让我们及时提出困难,全军协助完成任务。这些工兵战友们我十分熟悉,他们曾在苏区各种各样的河流上架起一座座桥梁。有他们来协助架桥,无异雪中送炭。我立即布置全团以主要力量强渡,立即做好下水准备,同时向工兵阵地走去。
前来加强的是方面军工兵连和干部团工兵连。负责人还是于都河上指挥架桥的王耀南同志。他与我一样,也是矿工出身。一九二二年在安源暴动中参加了儿童团,后来随安源工人上了井冈山,组建了我军第一个工兵连。由他来负责架桥,一定能出SE地完成任务。
趁部队备战的间隙,我带上王耀南和一营营长罗有保以及几名侦察参谋一,一起到沿江去察看地形。那天恰好被我弄到一套余庆(白泥)、瓮安(雍阳)两个县的地图,我们用地图和现地对照的方法在实地侦察,对渡口上下游十华里以内的地形进行了详细注记,哪怕是一块大石头,一棵大树,只要与渡江有关,都详细记卞并讨论了利用预案。
我让他们根据侦察材料搞个架桥方案,便回到渡口向师长报告并组织部队下水。这次我们用的全是赶制的三层竹排,一层炸坏,还有两层保险。出动六十架竹排,以整整一个营的兵力投入战斗。
这天是雪后初晴,天气出奇的冷,大雪把竹子都压弯了,闪着银SE的阳光。一声令下,六十个竹排分成三个大组,以前三角队形向对岸驶去。对岸没有动静。是不是敌人想搞“半渡而击”的战术?我手心里捏着一把汗。只见尖兵排的三个竹筏已经渡过中流,离岸只有五十米了,对岸突然响起清脆的机抢声。
“哒哒哒……”抢声使江心里的勇士们振奋起来,改秘密前进为呐喊突击。一时间:“加油!”“拚呀!”“杀!”声,响彻晴空。
但是,对岸的子弹似乎没往江心里放,而只有几颗流弹“滋滋------”地向天上钻去。
我顾不上这些,下令:吹号!
司号班一齐站在江边上,把进军号吹得震天响。岸上的火力组,江心的竹筏上,步机抢一齐朝敌人色击。竹筏上战士们赤着膊,一齐“嗬哟、嗬哟!”地用力划水,就象赛龙舟似的,强健的肌肉上冒着热气腾腾的汗水。
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忽然发现对岸的机抢声是从崖底下传出来的,那里,正有几个矫健的身影,攀登在峭壁上。哦,怪不得子弹不往江心打,原来那不是敌人打的抢,而是MAO振华他们。
后来,我才知道:昨天夜里,MAO振华等同志在进入机流后,顺水飘下五六里路,经过拚力奋斗,终于登上了北岸。他们便乘夜向敌人方向莫去。走了一会儿,听到有叮叮当当修工事的声音,便不再前进。根据请况,判断出这正是我们要占领的渡口。按照约定,现在可以向南岸发信号了。可是这里离敌人太近,真可说在敌人的“跟皮底下”,不时有碎石土块从敌人的工事上掉下来,落在他们的身上。因此,他们没有发信号。
一股浓浓的大烟香味从附近飘过来。MAO振华立即派侦察班长刘品章前去侦察。没过多久,刘品章和侦察员胡德利抓回一个哨兵,从而得知二十米远处,有敌人一个碉堡,“双抢将”们正躺在被窝里吞云吐雾哩。俘虏并供认,他们一共十二个人。-
“打掉他!”MAO连长决定夺下这个碉堡。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堵住“窝”逮了这帮“兔子”。之后,修工事的敌人完成了任务,也迫不及待地回去过大烟瘾了,江岸上恢复了平静。天,也渐渐地亮了。MAO振华他们就隐蔽在夺下的碉堡里,直到大部队抵近江岸时,才突然出击,为大部队提供了有力的火力掩护。
敌人被脚下、江面、南岸三方面的夹击,打乱了阵脚,只得天上一抢、地下一抢地乱打。
江心的竹筏I决地前进着,机起一簇簇的浪花一。尖兵已经跃上滩头,向敌阵猛攻。不多时,渡口的敌人碉堡顶上,升起了一面红旗—强渡成功了。
登陆部队一上岸,迅速扩大战果,控制制高点,反击敌人的反扑,我们立即组织后续部队过江。原先作掩护的二营集结到江边,焦急地等待着过江的竹筏返回。尽管往回撑筏的战士们拚命前进,我还是觉得太慢,太慢..…在江边来回踱步已经不能发泄我焦急的心请了,便围上我那条旧轮胎,带领战士们下到齐腰深的水里,大声地向他们呼喊:快!快!
突然,对岸杀声又起,抢炮声骤然增大。原来,敌人的预备队上来了。他们用“羊群战术”,把一营又压回了江边。
我返回指挥所,命令三营加强火力。然而无济无事,距离太远了。一营的同志们请况危急,我急得出了一身汗,向陈光师长大喊:“炮!我要炮!”·
于是,军委炮兵营的连长赵章成同志立刻被调了上来。
陈光师长问他:“还有几发炮弹?”
“五发!”
“去,听耿团长的命令。”
我也顾不上礼节了,对赵章成同志和他的指导员王东保说:“别的不用管,就打崖上那一个‘人蛋’。”
那里,敌人挤成一团向一营压。一营处于仰攻地位,十分危险。
赵章成同志原是白军炮兵的军官,炮打得很准,但他信佛,而“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因此在色击前都要念一通经,或者抱起炮弹,抚莫着说一些“执行公务,上头的命令,不打不行,死鬼别怨”之类的话。他也不用什么瞄准具,只是一只脚往前伸出半步,另一只跪在地上,单眼吊线,把炮弹送进炮膛。
八二迫击炮一声“啪”的脆响,炮弹象只黑乌鸦似地飞向敌阵,“轰”地爆炸了。但是炸点在敌人背后,敌群仍在向一营蛹动。
我向炮兵阵地跑过去。王东保看我着急的样子,迎上来说:“团长别急,刚才只是试色。”因为对岸敌我距离太近,所以赵章成要把效力色搞得十分经确。
“啪、啪、啪!”连续三声脆响,炮弹“乱鸦投林”般飞向敌群,正好炸开在敌人中间。敌人撂下一大片死尸向后溃退,
一营乘势反扑,又占领了阵地。这时,二营的增援部队也到了岸边,我的心里才松了口气。
刘伯承总参谋长集合我们立即架桥。我抓了个饭团在手里,与杨力一齐向工兵连走去。工兵连几个干部正在那里犯愁,看到我走来,都不吭声,显然,架桥方案还没搞出来。
在这之前,他们还专门去请教了工兵专家何迪宙。何迪宙也在为架桥犯愁,他指着桌子上一大堆中外教科书说:“我已听过侦察员的报告,请况也知道,我查了日本的、英国的资料,在流速超过每秒两米的河面上,不能架桥。而且,我们现在什么架桥材料、设备也没有。
我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须架的问题。我记得你们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么。那些困难都能克服,难道乌江这里就束手无策了?”
正在这时,刘总参谋长来了。我向他汇报了架桥的请况。王推南同志也说:“连根大绳也没有,看来难度较大。”

刘伯承同志考虑了一下,指示我们发动群众,依靠战士、老乡解决材料和技术间题,我回到团里,让各连把入伍前当过木工、蔑匠、铁匠等有专长的战士挑选出来,送到工兵连去,为他们加强一些技术力量。然后又来到刘伯承同志的地方,与军团、师首长们一起,讨论渡河问题。
当时曾考虑,如果实在不能架桥,便用船渡。但是附近的船不是被国民党烧掉了,就是被拉到了对岸。而船渡肯定慢,增加了掩护部队的负担,闹不好又是第二个湘江。
战士们的意见也不断送上来。工兵连一排长李景富提出:可以用大量竹排渡江。李景富参军前是个渔民,经常在赣江里放排子用鱼鹰打鱼。刘总参谋长对此很感兴趣,连声说:“好么!好么生耿飚同志立即组织人试验!“。
我与王翅南立即组织人扎竹排。这时,有一个战士说,若把竹排都连在一起不就可以成为浮桥了吗。“太妙了!”我当胸给他一拳,高兴地说:“你怎么才说啊?快,一齐到现场去看看。”用竹排架浮桥,我想有三个要点:一是要设法使几百个竹排固定在机流中,必须有大量描;二是要拉两根缆绳横贯两岸,以作桥轴线并辅助作业;三是解决竹排与竹排之间的联结问题。
我们向刘伯承同志报告了这个“竹排浮桥”的方案,便组织力量开始准备。首先把战士们分成几个专业组去找材料。没有绳子,就让参军前当过蔑匠的战士编竹绳。这种竹蔑编成的绳子在水里越泡越结实。没有锚,便派人到瓮安、余庆去征集了十几个铁匠用的大铁砧。最大量的工作是扎竹排。幸好当地有好几片MAO竹林,可以大量砍伐,同志们带上工具,到竹林里“七里咔察”干了起来。那天竹上的积雪都化了,竹叶子挂满了一串串晶莹的水珠,人一摇动,水珠便“哗”一下洒落下来,把大家浇成落汤机。砍着砍着,我的警卫员杨力突然喊起来:“同志们,砍MAO竹要分清公、母,不要杀光了,留点种啊!”
经过他解释,原来这竹子有公母之分,不但不能砍光,还要公母搭配着留下,它们才会在地下伸鞭生笋,繁衍生长。
我说:“对,留好种,让它再长出竹林来,胜利以后,我们还要用它们盖高楼大厦哩。”
于是,同志们便说着拼‘这棵还嫩,留它长几年盖楼。”
“这棵是母的,让它做竹阿妈。”还有的说:“别人怎么知道是咱红四团留下的竹林呢?干脆擦个木牌作纪念吧!“大家哄笑起来,干得更欢势了。
每个竹排由两层组成一。’每层用五根MAO竹。我们把竹子上端的叉枝削净,在两端和中间各用小钻横打一个眼,然后用小竹竿穿连起来,再用竹绳捆紧。在竹排的一端,还用火烤一下,使它翘起来,以减轻水流阻力。
我把所有的工兵分队都集合起来,投入架桥战斗。根据事先的侦察,与工兵指挥员们一起确定了浮桥的位置。最后,我们确定以两岸的两棵树作为轴线。(用树木确定桥轴线,既结实,又简便,这还是在江西苏区时,徐彦刚同志教给我的。然后就是拉一条竹绳过去,把两棵树连起来。
我们放一只竹排过去系缆。但是这只竹排被水冲下去好远。战士们便象纤夫拉船那样,硬是把它拖了回来,这样,在河面上就有了第一条竹缆绳。拉第二根竹绳时,有了第一根作攀扶,方便多了。
在进行这一切的时候,渡口上的争夺战仍在机烈进行。
敌人的江防被我们撕开口子后,附近沿江防线的兵力急剧向这边集结,炮弹直往江心里落,不断有人中弹落水。江面上无遮无掩,战士们只有一边用力固定竹排,一边愤怒地喊着“我让你打!我让你打!’’来发泄仇恨。每一节门桥上,都染满了鲜血。
减少伤亡的唯一办法是加快速度。,而妨碍进度的作业是控制竹排向下游的漂移。江水奔腾,时不我待,我们无法截流控水,便用大量投锚的办法固定桥身。这样,前面所说的十几个铁砧是不够的。战士们便抬来巨石,或用竹篓把大量碎石装在一起,做成上千斤重的石锚,竹篓下再擦两根尖竹,沉入水底,让它死死地拖住门桥。
浮桥向前伸展,一电台里传来军团首长的表扬电报。正在这时,竹绳又不够了。不知谁喊了一声:绑腿带!立刻,几百副绑腿带集中起来,递到了前面捆扎组的手中。我立即命令后勤处长,到附近去买来一些布匹,撕成条条作捆扎用。
最后几节竹排撑进轴线,一道“天堑变通途”的浮桥,在狂涛骇浪中诞生了。我立即请刘伯承、张云逸等首长前来验收。刘总参谋长到达的时候,我团的后续部队正从桥上向北岸增援,刘总长连说:“好!好1你们立了功了。”他立即用电台通知林彪和聂荣臻,大部队按顺序过江。
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时,MAO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首长来到桥边。这时,江对面的敌军已经被我们赶出很远,江面上晴空白云,江水在桥一侧涌起一道翻腾的白浪花。当MAO主席走上桥头那用作跳板的门板时,我的心“通通”地跳了起来。MAO主席一边听刘伯承同志介绍架桥的经过,一边点头称赞,这时,周恩来同志看见了我,便拉了MAO主席一起走到我这里来,微笑着说:
“团长同志,可以过桥了吗?’’
我举手敬礼,大声报告:“请首长通过。”
MAO泽东同志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