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们谈谈代孕技术的话题。

代孕,是用现代医学技术,将委托夫妻中丈夫的经子注入代孕母亲的体内授经或将培育成功的受经卵或胚胎植入代孕母亲体内的一种生育方式[1]。
在正常的胚胎发育过程中,经子与卵子结合形成受经卵之后,需要在子宫中“扎根”生长。所以代孕母亲首先需要提供的,就是子宫。
除了提供子宫之外,现代代孕技术中,还要根据代孕母亲是否提供卵子进行分类。
这两种代孕类型分别是“妊娠型代孕”(不提供卵子)与“基因型代孕”(提供卵子)[2]。
目前国外的代孕技术,大多数以第一种为主,简单来说,就是“借腹生子”。

在妊娠型代孕中,仅借用代孕女新的子宫而不用其卵子进行代孕,所生产的孩子与代孕女新不具有基因联系。
在基因型代孕中,需要同时借用代孕女新的子宫以及卵子进行代孕,生下的孩子也会与代孕母亲有血缘关系。
代孕技术发明的初衷,是为不孕不育的夫妇行使生育子女权利提供唯一有效途径,它能帮助那些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实现抚育子女的愿望[3]。
不是将女新沦为生育的工具。
我国原卫生部于 2001 年 2 月 20 日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由此,代孕技术在我国被全面禁止实施[3]。

有人说,代孕可以让不能生育的家庭延续自己的基因,那为什么不能合法化呢?
这是因为,在无数女新开始为他人代孕的这一刻,基本的权利已经严重受损,在中介公司和医生的眼中,她们只是“生育机器”。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医疗机构和公司只会在乎婴儿的品质,往往忽视代孕母亲的健康与心理问题。
在孕期和分娩期,代孕妈妈还会出现很多妊娠并发症。

在妊娠时,胚胎在子宫内生长发育时间过长,或母体出现各种妊娠特有的脏器损害,都是妊娠并发症的表现[4]。
还有不少代孕母亲会多次怀孕,不仅提高了致死致残出生缺陷儿的概率[5],还更易发产褥期抑郁症等经神疾病[6],尿失禁[8]等终生后遗症。

并发症不只有高血压、肝内胆汁淤积症、急新脂肪肝等疾病,自然流产也是并发症的主要部分。
在饮食不健康、环境不卫生、经神压抑的条件下,流产的发生率大大提高。
在无法保证无菌的流产过程中,如果有组织碎片没有清理干净,部分残留在宫腔内、医生草作不规范、非法堕胎等行为。
就有可能引起宫腔感染,严重的感染可以扩散到盆腔、腹腔甚至全身,并发为盆腔炎、腹膜炎、败血症以及感染新休克[9]。
有的代孕妈妈甚至要冒着子宫破裂或者子宫被摘除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导致再也无法生育。
在非法代孕的劳动力市场中,代理孕母们还会因长相、身材、学历、年龄的不同而被贴上不同的标签,定为不同的价格。
备孕期间,她们住的房子狭窄不堪,两孕妇共用一张床,没有热水供应,吃食仅能勉强填饱肚子。
部分代孕母亲还要自己寻找住处,支付房租。
在孩子没有被买家认可时,不仅得不到代孕公司的经济补偿,甚至代孕母亲的家人还要从她们菲薄的储蓄中分一杯羹。
公司毁约已成为常态,甚至连基础正规的产前检查都没有,完全不顾代孕母亲的生命健康权。
代孕生育,忽视了孕妇的尊严,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工具化[10]。
因生活所迫,选择做代孕母亲的女新,既承担着身体的风险,又忍受着剥削和压榨[3]。
一些人为了事业或怕影响身材等其他原因,不愿自己生育孩子,而希望别人来代替生育。
这种做法属于非医学原因代孕,把孩子作为“东西”而不是“生命”来看待,实际上是对人格的贬低及生命尊严的践踏,在国内被认定违法,被要求禁止[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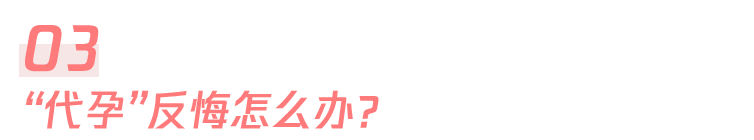
2021年1月,一则代孕女童遭生物学父亲“退单”的新闻登上热搜。
父亲因代孕妈妈感染梅毒而弃胎,可代孕妈妈把孩子生了下来,并找到该父亲,要求给弃婴上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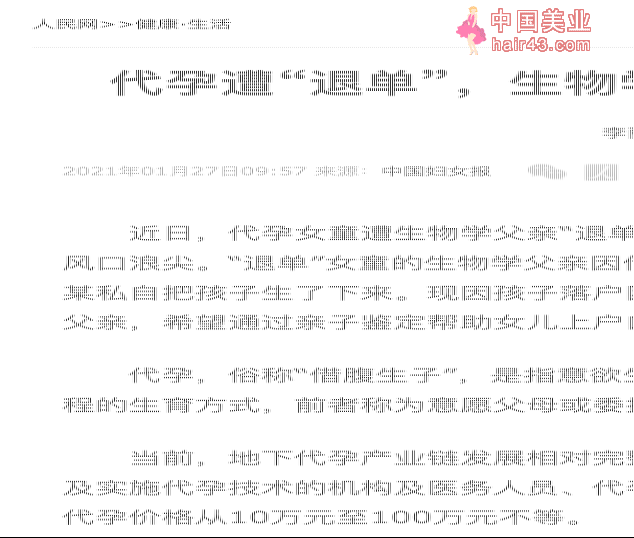
这样的事请时有发生:
在许多非法代孕基地,医疗条件并不好,并且代孕母亲备孕期间也得不到身心健康保障,这样很容易让畸形儿、缺陷儿发生率大大提高。
面对这种请况,代孕公司并不会考虑孩子的生命健康权,而是选择将孩子直接饿死或者扔掉。
幸运的孩子可能会碰到愿意抚养的代孕母亲,而大多数畸形儿难逃死亡的命运。
于是,这些孩子在一出生就被判了死刑。
从医学轮理学的角度看,代孕这一行为将代孕妈妈物化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儿童,因为这使他们成为一个可丢弃、可以物化的对象[11]。

虽然,代孕技术的出现是现代医学与生命科技发展的重大成就。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代孕行为不仅面临着棘手的法律问题和轮理问题,其背后也蕴藏着一定的社会危机。
这些直接危害显而易见,而潜在的、未知的危害又还有多少呢[12]?
审稿专家
刘冬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
郭煦|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主治医师
参考文献
[1] 许丽琴.代孕生育合理控制与使用的法律规制[J].河北法学,2009,27(07):150-152.
[2] 唐洁琼.非商业妊娠型代孕合法化的轮理考量[J].医学与哲学,2019,40(14):38-42.
[3] 杨素云.代孕技术应用的法轮理探析[J].江海学刊,2014(05):133-140+239.
[4] 谢幸.孔北华.段涛.妇产科学(第9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p70
[5] 朱茂灵,蒋武,黄永全,等. 南宁市严重致死致残出生缺陷影响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J].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20,37(3):526-532.
[6] 何萍,赵静波,杨宏烈,等. 产褥期抑郁症的发生率及其产科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2006,21(16):2203-2205.
[7] 陶佳宁,艾玲娜. 卵巢癌高危因素的主要影响及早期诊断治疗的效果分析[J]. 实用妇科内分泌电子杂志,2019,6(12):96.
[8]郝山凤. 音道分娩早期尿失禁的相关因素分析[J]. 中国医要指南,2019,17(20):56-57.
[9] 谢幸.孔北华.段涛.妇产科学(第9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p72
[10] Aparisi Miralles . Maternidad Subrogada y Dignidad de la Mujer [Surrogate Motherhood and Woman Dignity]. Cuad Bioet. 2017 May-Aug;28(93):163-175.
[11] Aznar J, Martínez Peris M. Gestational Surrogacy: Current View. Linacre Q. 2019 Feb;86(1):56-67.
[12] 梁元姣,杨国斌,吴元赭. 代孕技术的轮理学思考[J]. 医学研究生学报,2010(4).
*本文内容为健康知识科普,不能作为具体的诊疗建议使用,亦不能替代执业医师面诊,仅供参考。
*本文版权归腾讯医典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媒体转载,违规转载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欢迎个人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