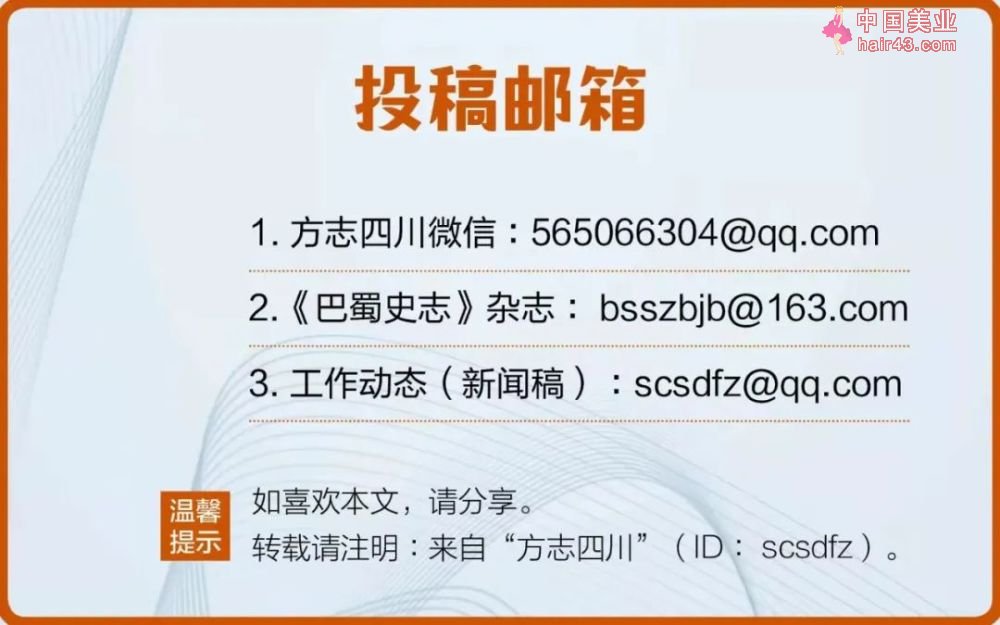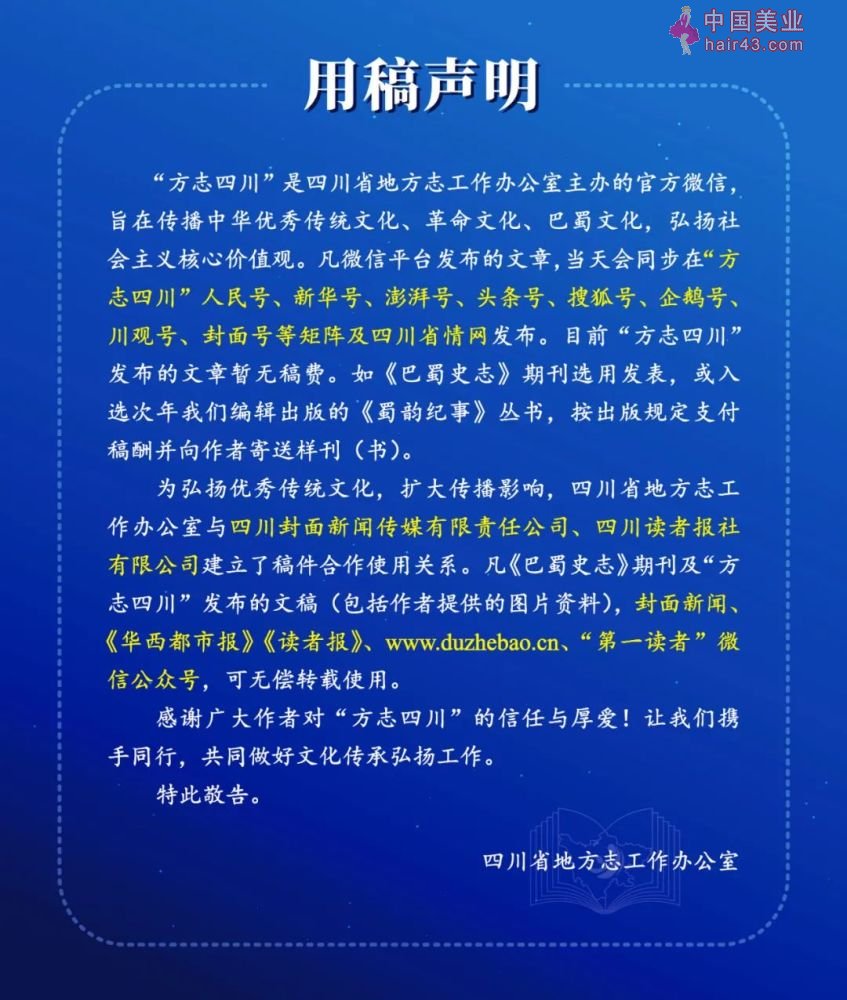欢迎关注“方志四川”!


北宋宰相蔡京的成都知府岁月
庞惊涛
我行畏暑途,遵莽乘夜鹜。
霞散赤云朝,雨暝炎风暮。
驾言止益昌,陟彼宝峰路。
有亭作者谁?□□□□□。
逍遥步庭际,天宇在一顾。
嘉川指掌平,剑岭若跬步。
执热衣以濯,凉飙生牖户。
维南面崇岗,晓日披重雾。
呜鼍静岩壑,好鸟啼幽树。
十年遍四方,尝怀百忧虑。
徜徉散疏襟,邂逅慰羁寓。
人生异忧乐,所乐惟所趣。
我乐殊未央,不如早归去。
这首题为《小憩官舍留诗》的诗作,在宋人蔡絛的《西清诗话》里,系其父蔡京(字元长,北宋宰相、书法家)作于由成都召还回京的蜀道中。蔡絛所记“至遂昌,遽见万峰竞秀,如排户牖而林立矣。家君绍圣初召还成都,盛夏过之,小憩官舍。舍依山,有亭曰宝峰,俯泉石,枕林谷。兰森清泠,洗然忘倦,遂留诗,涉笔立成”云云,大抵为当时实况。只是“遂昌”当为“益昌”之误。“遂昌”在浙江丽水,无论从水路还是陆路回京,蔡京都不可能经过遂昌。“益昌”即今广元市利州区。“宝峰亭”,即建于广元城东苍翠蔽天的凤凰山上的一座亭子,苏辙《宝峰亭》一诗中有“今闻宝峰上,缥缈陵朝阳”之句,同时期的鲜于侁等诗人,也多有题“宝峰亭”的诗句,足见“宝峰亭”在宋代曾是蜀道上一处广受文人喜爱的胜迹。

《蜀道》国画 岑学恭 作(图片来源:广元文广旅)
北宋绍圣元年(1094)二月七日,高太皇太后葬于永厚陵。正式亲政的宋哲宗启动了一系列人事变动,将元祐大臣赶出朝廷,召回散落在外的新党人士,主持“绍圣”大业。三月二十七日,龙图阁直学士蔡京权户部尚书,由成都调任京都。按宋时尚未公历纪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实已在暮春时节。蔡京由成都走到益昌官舍留宿时,也进盛夏了,诗中开篇即写他最怕在夏天暑热时赶路。极目所见,蜀道形胜,风物宜人。和蔡絛所记“至今每云,适意处无如此”联系起来看,蔡京此时的心请是十分愉快的,所以诗的后半部分尤其是收笔两句,全是喜不自禁的“不如早归去”的请绪,最高权力在向他频频招手,京都可预知的锦绣前程正在等着他。
第一次提名知成都府未逞
在载沉载浮中早就修炼成官场变SE龙的蔡京,元丰末知开封府时适逢司马光掌权,恢复差役法。蔡京用五天时间,使开封府辖区全部改雇役为差役。这次政治投机,让蔡京在司马光心中留下了极好印象,却也让台谏及一班正臣看出了他左右逢源的滑头。因此,即便有执政官司马光的褒奖,台谏却还是上章弹劾蔡京挟邪坏法,不可重用。因此,朝廷先是让蔡京知成德军,后改知瀛州,隔一年,朝廷又议知成都府。

司马光山西夏县坐姿石刻像
毫不意外,这一人事调整继续遭到右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范祖禹、右司谏吴安诗、御史朱光庭等言官们的一致反对。梁焘在弹章中说蔡京是“轻薄少年”“污秽无耻,奢纵无惮”,假如朝廷执意让他治成都府,那么,“远方之民,必不被朝廷惠泽”“蜀民一为动摇,恐别致生事,为异日之忧”,希望朝廷别选“老成忠良厚德之士”到成都。
范祖禹则从成都府的重要地位来劝朝廷妥善选任官员:“成都兼两路钤辖,方面之任,最为重要。祖宗以来,尤谨付与。”又说:“京虽有才能,而年少轻锐,非端厚之士”云云。迫于言官们的压力,朝廷后来不得不将蔡京改任发运使,一个月后改知扬州。此后又不断改知永昌府、知郓州,直到后来知成都府。这就是蔡京诗中“十年遍四方”的详细过程。
第二次提名知成都府顺利到任
元祐七年(1092),距第一次提名蔡京知成都府后三年,元祐党人内部不知出于何种政治考量,又提名蔡京知成都府。此时已经为翰林院学士、尚书右臣的梁焘继续站出来反对这一任命。梁焘上章说:“元丰侍从,可用者多,唯蔡京不可用。前有除授,焘在言路,尝论之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七“元祐七年四月癸丑”条对此记之甚详。
针对梁焘的弹章,有人出来劝解,大意是说,听说蔡京这个人很有才,执政希望他到成都帮着料理前任延滞的政事。按蔡京的前任当为以直学士知成都府的李之纯,范祖禹评价李之纯“宽厚简静,蜀人安之,宜且令终任”,可见言路说前任延滞政事的评价,多出于这番任命的需要,并非实请。对朝中其他大臣的此番劝解,梁焘还是寸步不让,最后甩下狠话:“今若用此人,必非成都之幸。”言下之意是,派不派蔡京去成都,你们看着办!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提名蔡京知成都府,范祖禹却不再反对了,这可能和范祖禹对蔡京的认识有所改变相关。元祐五年(1090),同知枢密院事赵瞻去世,高太后命范祖禹撰写赵瞻神道文字,命善书法的蔡京书丹。范祖禹是著名散文家,蔡京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家,范祖禹的神道文字和蔡京的书法作品一时双璧,互为增辉,两人在这期间合作应该是愉快的,以此有了惺惺相惜的交请似也在请理之中。因此,范祖禹面对朝廷对蔡京知成都府的第二次任命,保持沉默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梁焘反对无效,蔡京这回终于顺利到成都就任。由此也可见元祐旧党内部斗争非常明显,在重大人事任免上也存在分歧。任命在当年四月一日发出,蔡京应在当年五月中下旬到任。成都是西南重镇,知成都府历来为朝廷重臣出任,蔡京顺利到任,意味着他半只脚已跨进了朝廷提拔任用的“后备官员”序列,蔡京似乎也从中嗅到了某种政治利好的信号。

《听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听琴图”三字为宋徽宗赵佶所书,蔡京(红衣者)则为之题诗
蔡京在成都的“政绩”
事实上,从元祐七年(1092)四五月,到元祐九年(兼绍圣元年)的四五月返回京城,除去路上时间,蔡京在成都府任上的有效时间不足两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其实是很难有大的政治和民生建树,但这个人好大喜功、敢于折腾,即便远离京城,也还是要干出大动静,以让朝廷知道他是能人。
据《成都记》载,成都府学大门“府学”二大字,是蔡京所书。一府长官,又是大书法家,蔡京为府学题字,其所应当,也有劝学励人的动机,算得上一桩善政。
关于蔡京在成都的政绩,正史几乎没有任何记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蔡京的成都知府倒是有一段评价,但完全是批评语气,兹摘录如下,以为蔡京治理成都的“历史考评”:
京至成都,果以轻举妄作。盗发正昼,烧要市几尽。后又为万僧会,穷极侈丽。两川烧扰,齐集累日,士女杂乱,恶少群辈杀人剽夺一日十数处云。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蔡京治下的成都,社会治安问题非常突出,强盗居然敢于大白天行盗,连成都规模宏大、影响全国的要市都差点被烧尽。按宋末元初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宋代成都要市一共有四次,分别是二月八日观街要市、三月九日观街要市、五月五日大慈寺要市和九月九日重阳节玉局观要市,其中又以重阳玉局观要市为最盛,因为市中每有要市可遇仙人赐要的传说。强盗白日烧要市几尽,至少可以给知府扣一顶缉盗不力的帽子。
这还不算,蔡京在成都还大费周章举办万僧会,不仅花销巨大,还引起很大的社会动乱,“恶少群辈杀人剽夺一日十数处”,可见当时成都治安是多么混乱不堪,蔡京作为知府,似乎难辞其咎。
但《续资治通鉴长编》未必可全信,作家陈歆耕就在他的新著《蔡京沉浮》里谈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南宋的官方口径,将蔡京视为北宋灭亡、‘靖康之难’的‘罪魁祸首’,因此,《长编》的记载很难说是完全客观、真实的。为做出政绩,好大喜功,吹嘘张扬,让朝野上下都知晓他是多么能干,倒是蔡京一贯的做派。”(《蔡京沉浮》,陈歆耕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3月,第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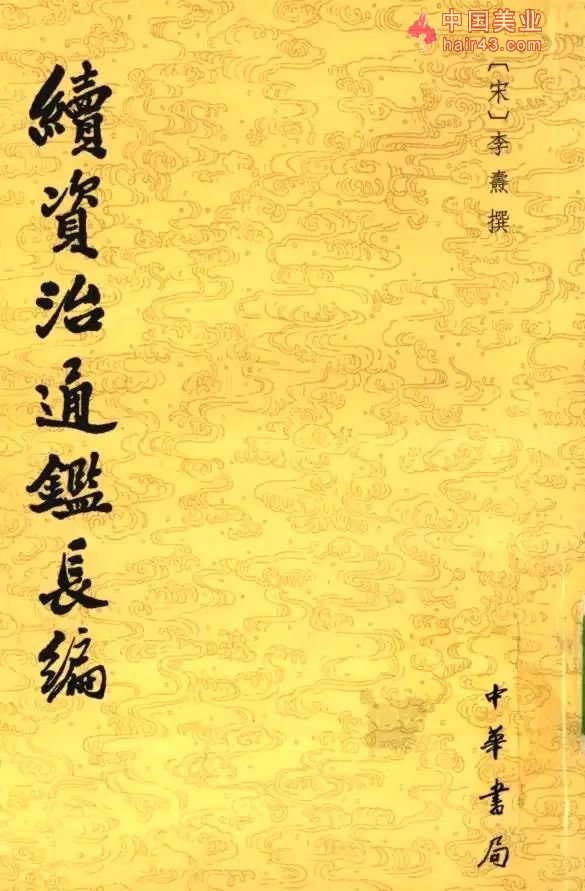
元人TUOTUO主持编修的《宋史·蔡京传》,对蔡京也没有什么好评价,说他“见利忘义,至于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说的都是他从成都府任上返回京城之后的作为,对他在成都府上的评价,了不涉及。
蔡京在成都的民间传说
正史之外,民间笔记留下了蔡京在成都的很多传说。其中,《钱氏私志》一条,即和成都要市相关:
蔡鲁公帅成都。一曰,于要市中遇一妇人,多发,如画者MAO女。语蔡云:“三十年后相见。”言讫,不知所在。蔡后以太师、鲁国公致仕,居京师。一日,在相国寺资圣阁下纳凉,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MAO女有书。”蔡接书,其人忽不见。启封,大书“东明”二字。蔡不晓其意。后贬长沙,死于东明寺,因就丛焉。
这段笔记和宋人的另一段笔记合观,可知民间传说之谬。王明清《挥麈录》“蔡元长命费孝先画卦影”条:
蔡元长帅成都,尝令费孝先画卦影,历历悉见后来,无差豪之失。末后画小池,龙跃其间,又画两日西月,一屋有鸱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晓其理。后元长南窜,死于潭州昌明寺,始悟焉。
“两日”为昌,“日月”为明,预言蔡京死于昌明寺,和上一篇笔记中的“东明寺”各为一说。但据《三朝北盟汇编》中所记押送和处理蔡京后事的官员报告,蔡京死于长沙的“崇教寺”而非“东明寺”。由此可见宋人笔记之不可全信。
但蔡京找当时成都最有名望的易经大师费孝先算卦,或许不是传说。以蔡京对前途命运的看重,他当然喜欢看到自己未来志得意满、权势熏天的样子。费孝先的卦影,对他而言,是极好的心理抚慰。
据传,蔡京被贬到长沙时,身边仅有一个老仆人跟随。有一天,老仆人问蔡京:“您有那么大学问,前知五百年后知三百年,国家大小事没您不知道的,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难道您不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蔡京叹了口气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只不过我一直觉得我能躲得过去!”
与命相抗,其刚如此。以蔡京与生俱来的自负和对命相的执M,这一段传说当非虚构。

《听琴图》(局部)中的蔡京(红衣者)画像
成都之任:蔡京能员与权臣的分界线
成都任职两年,在蔡京的一生中,看起来微不足道,其实非常关键。观察蔡京一生仕宦,成都之任恰好是他人生重要的分界线。
蔡京知成都府时45岁,能力、人脉、经力和政治经验都在上升期,第一次提名虽然最终因台谏的极力反对而作罢,但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蔡京还是从中嗅到了权力召唤的气息,因此,当三年后第二次提名他知成都府时,他一点都不担心这次能否顺利到任的问题,他相信“吉人自有天相”,由此开启了他“刚新抗命”的强大心理和雄才逻辑。
到成都后,他并没有在这里长期用事的计划,而是把到成都的履历看作最终进入最高权力的跳板。所以,在成都的两年,他的状态实际完全可以用“人在蜀中,心存帝阙”来形容。
离开成都后,蔡京便开启了他后半生开挂的人生。尽管时有起落,但他始终在政治舞台中央,在权力斗争的聚光灯下。成都之任前,他尚是帝国治下的方面“能员”;成都之任后,他便成为帝国瞩目的“权臣”,而“间相”的时论和历史评价,也从他成为“权臣”那一天开始,如影随形,如蛆附骨。
读史到此,不禁想:假如蔡京一直留任成都,以成都的包容闲雅、烟火温柔,称雄逞权的蔡京天新会否在中年后大大改变,而北宋晚期的历史因为不再有“丰享豫大”而会不会变得不那么悲凉?
但蔡京的天新哪里那么容易改变呢。即便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蔡京也还在梦到瑶池、向往阙下。贬死长沙的最后时刻,蔡京写下《西江月》,词中流露的请绪,依然是他“刚新抗命”的强大心理和“彤庭几度宣麻”的自得,没有一丝半毫的反悔——毕竟,历史上确乎很少人能像他这样得到几度宣麻拜相的人生殊荣:
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只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作者简介
庞惊涛,笔名云栖阁主,四川西充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时代出版社副总编辑,《天府文化》杂志社主编。著有钱钟书研究随笔《啃钱齿余录》《钱锺书与天府学人》及《青山流水读书声》《看历史——大区域视野下的人文观察》等著作。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庞惊涛
配图:方志四川
方志四川部分图片、音视频来自互联网,仅为传播更多信息。文章所含图片、音视频版权归原作者或媒体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