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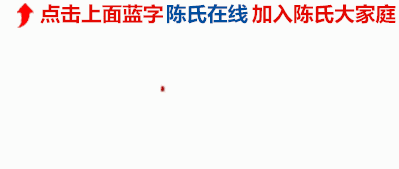
传家风丨扬正气丨铸族魂丨促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

陈独秀北京故居门口

北大红楼里陈独秀的办公室

陈独秀北京故居院内

蔡元培(前排左二)、陈独秀(前排左三)、梁漱溟(前排左四)等在北大合影。 资料图片
民国初年,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核心,许多颇有才华的作家渐次聚拢在北京,他们共同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五四”一代的带路人无疑当推陈独秀,鲁迅曾回忆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有力的一个。”从1916年11月到1920年初,陈独秀在北京生活了不过三年多一点,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直接组织领导了震古烁今的“新文化运动”,间接影响带动了“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此从陈独秀一生的思想轨迹来看,在北京的这段经历可谓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西河沿胡同里的邀请与允诺
前门西河沿街位于北京正阳门以西,现在这里还保留着不少民国乃至满清时的建筑。胡同西口的正乙祠是清朝康熙年间浙江商人修建的银号会馆戏楼,历经三百余年,现在是中国最老的、且保存基本完好的纯木结构戏楼;胡同中段路北一座二层小楼,门楣上“察哈尔兴业银行”的字迹清晰可见;不远处一座形制相仿的二层小楼,中间的宅门明显是被封上的,门楣上的字已然不甚清晰,旁边的标牌上提示这里曾是一家眼要店。尽管离前门、大栅栏近在咫尺,但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曾经是聚集了金融业、旅店业、餐饮业的繁华热闹所在,想必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初到北京就住在这条北京最早的“金融街”上。
1916年11月28日,37岁的陈独秀住进了北京前门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馆,同行的还有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汪孟邹。这是陈独秀第一次北上进京,之前他一直在日本、上海、安徽等地办报,此次进京也本是为了将亚东图书馆、益群书社合并改为“大书店”。但是蔡元培的造访显然改变了陈独秀的原定计划。西河沿的南边便是书肆云集的琉璃厂,陈独秀自然免不了要去“打卡”。巧的是,在琉璃厂陈独秀碰到时任北大教授的老友沈尹默,沈尹默又把这次巧遇讲给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的故交、时任北京医专校长的汤尔和。沈、汤都是蔡元培信任而且倚重的朋友,他们都向蔡元培举荐由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对于陈独秀和他办的《安徽俗话报》“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再加上汤尔和还拿着几册《新青年》告诉蔡元培“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这越发坚定了蔡元培“决意聘他”“与之订定”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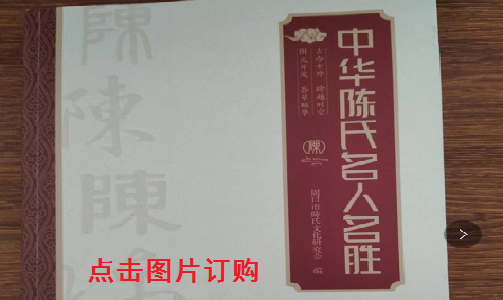
当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出任北大校长,就在当天早上9点,蔡元培专程到中西旅馆来拜会陈独秀,力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可陈独秀却以正在办杂志为由回绝了,蔡元培则表示可以把杂志一起带到学校里来办。据同行的汪孟邹记述,“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经过几次这样“三顾茅庐”式的邀请,陈独秀最终应允下来。由办报到办学,从游荡皖沪到定居北京,西河沿胡同里同蔡元培的几番会面直接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轨迹,这对陈独秀来说是有转折意义的。
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陈独秀“弱冠以来,反抗帝清”,武昌起义期间一度参政,护国运动当中坚持“倒袁”,先后署理《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甲寅》以及《青年杂志》。多年从事民主革命的政治挫折使陈独秀深感中国陷入“生机断绝”的境地,而之所以迟迟无法摆TUO亡国的危机,主要在于中国人“漠视国事”“殊令人心寒”。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陈独秀可能是最早开始反思“国民新”问题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陈独秀深刻意识到要想改变国家的命运,必先开启民智、争取民权、改变民新,必须从思想文化层面彻底地重塑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他看来,这才是最为长远的问题,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也是他日后与《新青年》同人一拍即合的关键,是他贯穿于办报、办学过程的思想线索。
坐镇箭杆胡同,影响一代青年
1917年1月1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专函回复了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提出的请求,批准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月15日陈独秀走马上任。哲学系学生冯友兰曾回忆说:“他(指蔡元培)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陈独秀到任之后,“文科的教授也多了,学生也多了,社会对于文科也另眼看待。学校是变相的科举的观念打破了。学生中间,开始觉得入大学的目的是研究学问,并不是为得个人仕途的‘出身’”。
不久陈独秀将家眷和《新青年》编辑部全都安顿在东城的箭杆胡同里,1917年2月1日发表《文学革命论》时,陈独秀已经住进这个小院了。箭杆胡同往北不远便是北大,当年这一带是北大三院学生宿舍。胡同其实有些偏僻,不知从何时起,胡同东段已经堵死,成了个死胡同,整条街上只留下了陈独秀曾经住过的院子。院子原本分东西两个部分,西院为房东居住,东院租给陈独秀,陈独秀和高君曼以及陈鹤年、陈子美住在南房,将北房留给《新青年》做编辑部。在建党百年之际,经过腾退、修葺,箭杆胡同的这处陈独秀故居已面向公众开放,去年伴随着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一时间游人如织。
陈独秀最初计划试干三个月,但实际做了有两年半,在北京期间,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个偏僻胡同的小院里度过的。陈独秀的生活并不算宽裕,但与李大钊、胡适在北京时的多次迁居不同,陈独秀很快就租下了箭杆胡同的这套院子,直到他后来黯然离京,其间一直没有搬过家。这似乎也说明陈独秀在北大备受尊崇和优待。从薪酬薄上可知,陈独秀300元的月薪虽然略低于理科学长夏元瑮的350元,但名字排序却仅在校长蔡元培之后,位居第二,并且300元的薪酬也仅次于蔡、夏,在全校排第三。1918年10月,北大红楼建成,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办公室在二层楼梯口左手边南侧第一间,非常宽敞,光照甚好。
随着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到来,从1917年4月起,周作人、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鲁迅等先后在北大执教,不难想象,新文化运动的同人们会频繁出入于箭杆胡同,小小的庭院在历史上却曾是鸿儒聚首的地方。《新青年》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假如没有《新青年》及其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在北大校园之外也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也正因此,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正是由北大和《新青年》,尤其是箭杆胡同时期的《新青年》这“一校一刊”双轮驱动的。而为这双轮掌舵的当然是陈独秀。胡适曾说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的特别新质是他一往直前的定力”。鲁迅虽戏称自己当时的创作是“遵命文学”,“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但却又很严肃地讲道:“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尊奉的命令”,“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陈独秀脾气火爆、新格执拗,颇有“家长制”的作风,这并非毫无来由。英文系学生许德珩和陈独秀之间曾有一桩趣事:陈独秀整顿课堂纪律,他“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把黎元洪侄子的缺勤记在许德珩头上,许德珩“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砸碎了布告牌。陈独秀大怒,因之又记过一次。许德珩再次砸了布告牌,并且站在陈独秀办公室门前搦战,要同他说理。此事立刻为蔡元培所知悉,经蔡调查,搞明白了原来确实是陈独秀弄错了,责令陈收回成命,好言劝慰。陈独秀为人刚劲、猛毅,同文质彬彬的蔡元培、胡适等绝不相类,但也正是这种新请使得他无论蒙受什么样的挫折和打击,仍时时蓄存着相当的决心和信心,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坚决和凌厉同各种守旧势力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包括在日后抓住历史机遇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和许德珩后来冰释前嫌,1919年冬陈独秀出狱之后,许德珩还受李大钊之托帮陈独秀在上海寻找房子。后来,陈独秀客居江津,许德珩还多次去探望,从中也不难看出许德珩对陈独秀的敬佩。事实上,陈独秀为人处世上虽然有强势的一面,但也颇有海纳百川的一面,新文学同人其实并非那样亲密无间,尤其胡适同其他几位的关系都很一般,假如没有陈独秀的领导、维系,很难想象北京时期的《新青年》能大获成功,产生空前的影响。
1918年1月,《新青年》正式改为同人刊物,由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陈独秀、胡适等六人轮流主编,“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有研究称,《新青年》在创刊之初发行量大约在一千份左右,1917年之后“销数渐增,最高额达一万五六千份”。《新青年》的读者数量可能比这个销售额还要多,比如像先前汤尔和拿着几册《新青年》给蔡元培看,类似这样一份刊物几人传阅的请况,在清贫的学生群体当中恐怕要更多,因而到底有多少人受到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影响、鼓舞,实在难以确数。MAO泽东后来曾讲:“《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从训蒙树人的目的出发,陈独秀特别看重音乐、体草等美育的方式与内容,认为传统教育重德育、轻智育和体育,“都把音乐、体草,当作无关紧要的学问”,“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促弱种的一个原因”。陈独秀的这种看法似乎也引起了青年MAO泽东的兴趣,他以“二十八画生”为名,将自己写的《体育之研究》寄到箭杆胡同,陈独秀将其发表在1917年4月出版的第三卷第二号《新青年》上。
在北大校内,陈独秀推行了一系列课程、制度改革,大力支持文科师生成立各种研究社团;在校外,他以《新青年》为思想文化阵地,旗帜鲜明地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轮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孔教,礼法,贞节,旧轮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进步思想得以迅速传播,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虽然陈独秀“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事实上,在他的影响之下,一大批才识卓著的青年人前仆后继地投身到救亡图存的队伍中来。
米市胡同所见证的思想转型
除去西河沿、北大红楼和箭杆胡同,北京城里还有几处也和陈独秀密切相关,而且还见证了陈独秀的思想转型。其中一处便是城南菜市口附近的米市胡同。1918年,为了出版《每周评论》,想必陈独秀也曾多次出入这里吧。
陈独秀很早就关注社会政治斗争,而且还直接参与过拒俄、反清、倒袁的活动,这和许多知识分子的经历大不相同,作为一个经历和经验都非常丰富的宣传家,在民国初年“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氛围里,陈独秀是不可能完全回避政治的。在箭杆胡同里编辑《新青年》时,他就发表过不少指点江山的文字。1918年11月,伴随着欧战结束,国内一时陷入“公理战胜强权”的狂欢之中,蔡元培、李大钊等纷纷发表演讲、撰写文章,他们都属意那些被压迫的劳工、庶民。特别是李大钊,展望着“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型已经非常明显。国内汹涌的爱国热请使得陈独秀认为“不谈政治”的“戒条”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从而决心再创办一份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介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政治讨论中来。
11月27日下午,陈独秀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了李大钊、周作人等人,议定编辑出版《每周评论》,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每周日出版,8开4页,一直持续到第二年8月30日被北洋政府封禁,共出37期。刊物发行所就在米市胡同79号院、原来的安徽泾县会馆里。米市胡同形成于明朝永乐年间,迄今已经有六百余年历史了。满清时期,米市胡同所处的宣南一带修建了大量的会馆,康有为曾住过的南海会馆也在这条胡同里。令人遗憾的是,进入新世纪后不久,米市胡同就消失在城市改造的轰鸣与等待之中,泾县会馆早已被夷为平地,康有为故居也前途未卜。
《每周评论》的创办显然是陈独秀思想转折的重要体现。在编辑《每周评论》期间,陈独秀以“只眼”为笔名就裁兵、禁烟、废督、组织国会、南北议和等国内的政治问题频频发表意见,而且在他的指挥下,《每周评论》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山东问题与巴黎和会,而这恰恰是时局的热点、焦点所在,《每周评论》也因此迅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其中即包括孙中山委派专人创办的《星期评论》《建设》以及MAO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
1919年4月底,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遭到彻底失败,“公理战胜强权”的M梦完全破灭,受《新青年》《每周评论》影响的青年学生在机愤之中聚集起来,在蔡元培、陈独秀的组织、策动下,“五四运动”随即爆发!在“五四”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陈独秀愤然戳穿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在随后的几期中,他不断发表文章抨击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召唤国民的爱国之心,铿锵有力地提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短短两年的时间,得益于《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广泛传播和进步思想的深入影响,陈独秀成为一时的焦点人物,从之前的经神领袖、文化偶像开始朝着政治领袖、社会经英转型。不同营垒对他的评价也开始两极分化。拥戴者称赞他是“思想界明星”“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敌视者则极尽诋毁、中伤之能事。比如1919年2月17日,主张维新、忠君保皇的林纾发表《荆生》,以田其美、金心异、狄莫分别影色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说他们三个人在陶然亭发表反孔言论,遇到“伟丈夫”荆生,对三人严加训斥、大打出手,田其美等批滚尿流,落荒而逃;稍后又作《妖梦》,以田恒、元绪、秦二世暗指陈独秀、蔡元培和胡适,其中田恒“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他们游历音曹地府,最终被阿修罗王抓住吃掉,“积粪如丘,臭不可近”。在茅盾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里,霸占善堂的赵守义把“陈独秀”唤作“陈毒蝎”,这些都反映了文化保守势力对陈独秀的敌视。
1919年3月26日晚上,迫于压力,蔡元培与“关系诸君”在汤尔和家中会商,讨论陈独秀在北大的去留问题,“十二时客始散”。会上,汤尔和、沈尹默的发言都极不利于陈独秀,这恐怕是最让人费解与唏嘘之处,因为当初正是他们二位向蔡元培举荐陈独秀。不久陈独秀便被变相免去了文科学长的职务,可谓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腹背受敌。“五四”之后,因为学生抗议声浪巨大,整个形势急转直下,陈独秀明知“在京必多危险”,但仍坚持抗争,6月11日午后,在北京“新世界”游乐场散发指导“六三”运动的《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当晚,箭杆胡同陈宅亦遭查抄。
“新世界”游乐场大致位于现在北京万明路、香厂路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民国初年,朱启钤在这一带仿照上海的“大世界”打造北京的“新市区”,繁华热闹一时无两,后世有人认为具有“把北京从封建都市改建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意义,位于十字路口东北角的“新世界”游乐场和西北角的东方饭店便是这个宏大工程的产物。想必也正是因为游人如织,所以陈独秀才选择在这里散发传单的吧。现在,万明路、香厂路的十字路口与寻常巷陌无异,只不过东方饭店还屹立在原址,并且还加盖了新的大楼,而“新世界”则显得命运多舛,如今占据原址的是一幢普普通通的高层塔楼,让人无可凭吊。
陈独秀案震动一时,社会各界纷纷声援,李大钊痛斥曰:“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明?”迫于压力,三个月后北洋政府释放了陈独秀。转过年来陈独秀曾短暂南下,返京后由李大钊护送于1920年2月离京避难,随后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一段常常被人传颂的佳话。陈独秀对欧洲尤其是法国思想文化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很早就了解到社会主义学说。随着局势的发展和《每周评论》的创刊,陈独秀的思想已经发生很大转变,例如他曾讲:“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地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当然,相比同期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专门、深入的介绍、讨论,陈独秀很明显是滞后于李大钊的,至少不像李大钊那样已经从个人意识中的关注、倾心转换为有目的的研究、宣传。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发表了包括著名的《研究室与监狱》在内的一组“随感录”,提醒大家“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M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三天后,陈独秀被从研究室抓到了监狱中,经过三个多月的思考,出狱之后陈独秀明确提出要“和过去及现状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这或许可以视为已经具备了建立新型政党的思想冲动;紧接着他还指出“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那些“没有财产的”被剥削、被压迫者要“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由此可见,在离京之前,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已经相当靠近了。
离开北京之后,陈独秀在上海重组《新青年》编辑部,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改版为党的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党的创建做了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的准备。历史的新局由此渐渐展开。
党的早期组织最先是在上海成立的,但思想的火种却是从北京点燃、传递过去的。陈独秀在北京的三年多时间里说不上春风得意,北京时期的陈独秀总给人一种“未完成”感,“新文化运动”仍然时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扑,“五四”所开启的民族自强、复兴之路尚前路漫漫,所以回想起这一时期的陈独秀总让人有一种壮志未酬的遗憾,这似乎正应了他早年写的一句诗:“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在陈独秀去世80周年之际,踏着陈独秀在北京的足迹,敬佩、惋惜、欣慰似乎都兼而有之,可谓五味杂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