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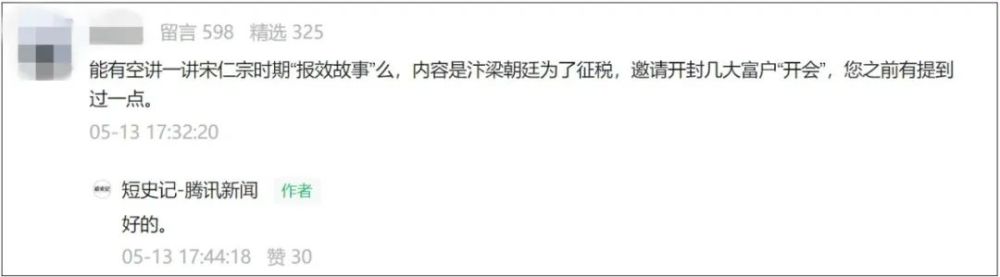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宋仁宗强行向开封富户借钱之事。
此事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六。是官员梁焘在呈给宋哲宗的奏章中披露的。
时为元祐二年(1087)。梁焘上奏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宋哲宗对开封百姓实施财产清查与收入管控。
此事须追溯到王安石变法。变法中有一项“市易法”,由名为“市易务”的新机构主持,专职负责以略低于民间高利贷的利息给商户贷款,商户须以房屋等固定资产做贷款抵押。这项政策推行之后,很快便变成了一场强制摊派。朝廷对市易务的考核标准是贷出多少钱,收到多少利息;市易务拥有各种“合法伤害”商户的权力,于是各种强迫需要钱的商户贷款,也强迫不需要钱的商户贷款。这种强制贷款行为与王安石变法中其他破坏商业环境(主要是政府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政策的合在一起,导致包括开封城在内的北宋大小城市皆百业萧条。百业萧条后商户们普遍还不起钱也交不起利息,于是市易务贷出去的许多款项就都成了烂账。宋神宗没有办法,只好允许这些商户将还款期限延长三年,每月定时向朝廷还一笔钱。可是即便如此,到了宋哲宗时代,烂账仍然还是烂账。于是宋哲宗决定通过财产清查和收入管控来对付这些欠朝廷钱的商户,直到他们将钱和利息全部还上。
梁焘反对宋哲宗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只会进一步恶化开封城的商业环境。为了增强反对的说服力,他提到了宋仁宗时代的一段往事:
“祖宗之朝,京师之民被德泽最深,居常无毫发之扰,故大姓数百家。庆历中,西鄙用兵,急于财用,三司患不足者数十万,议者请呼数十大姓计之,一日而足,曾不扰民,而国家事办,祖宗养此京师之民无所动摇者,正为如此。”
所谓“庆历中,西鄙用兵”,指的是宋仁宗时代与西夏的战事。李焘披露说,当时朝廷没钱支撑战事了,有数十万贯钱的缺口,有人建议将开封城里有钱的数十户大姓召集起来,结果在一天之内就把军费缺口给补上了。李焘讲这段往事,是想提醒宋哲宗:优待京城百姓,让他们发育成富户,对大宋政权本身是有好处的,朝廷紧急需要钱的时候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取。搞财产清查和收入管控,将开封城的商户都B破产,是得不偿失的。

宋仁宗像
梁焘没有细说朝廷是如何“呼数十大姓计之”的。
但在上一年(1086),另一位官员傅尧俞在给宋哲宗的奏章中偷露了部分真相。他说:
“庆历中,羌贼叛扰,借大姓李氏钱二十余万贯,后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顷岁,河东用兵,上等科配,一户至有万缗之费,力不能堪,艰苦万状。”(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八)
“羌贼”即李元昊的西夏政权。傅尧俞说,宋仁宗时代为了凑足对西夏用兵的经费,朝廷向富户们借了很多钱,其中仅李氏一家就借了二十余万贯。这些钱最后没还,只给了这些富户几个“京官名目”,就算两清了。“京官名目”对朝廷来说不算成本,几十万贯资财对百姓而言却是实打实的家产,富户们显然亏惨了。傅尧俞还提到,这类请况发生了不止一次。比较近的一次是河东发生战事(可能是指宋神宗时代由河东出兵进攻西夏),朝廷再次向富户们伸手,标准是每户摊派万缗(缗等于贯)。很多人负担不起这笔钱,困苦不堪。
被宋仁宗强行“借”了二十余万贯的大姓李氏,有可能就是梁焘提到的“数十大姓”中的一户。当然,因宋仁宗朝对西夏的战事持续多年,也有可能实际上是两次不同的借款。
需要注意的是,傅尧俞披露这段往事,并不是要否定北宋朝廷向富户伸手这个行为。
恰恰相反,和梁焘一样,傅尧俞也是想用这些事例来规劝宋哲宗不要竭泽而渔。他后面紧接着说:“此皆以上下全盛之时,取于民以为助,犹或如此,况今民力疲弊,国家指以为用而不忧者,免役宽剩钱耳,盖有时而尽,乌能持久?”——仁宗皇帝向大姓李氏等“借钱”数十万贯也好,河东用兵向富户摊派平均达万贯以上也罢,这都是本朝全盛时期的请况。全盛之时朝廷尚且需要向百姓伸手求助,何况如今已是百业萧条民生凋敝。国家能够指望的收入只有“免役宽剩钱”(王安石变法后新增的税种)了,这笔收入最终也会有枯竭的一天,是无法持久的。
傅尧俞希望朝廷能改变财税政策,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常规的茶、盐、酒税上面,而非以变法为名设立诸多新税种,同时打击官员挪用,严禁胥吏科扰百姓。否则,“臣恐数年之后,或至不足,一有缓急,将全取于民,不惟人难克当,必致误事”——要是不这样做,那再过几年,财政收入恐怕就要出大问题,遇上点什么大事,就不止是像以前那样只有部分缺额,只需向富户们伸手,而是财政一点钱都拿不出来,全都得临时向百姓们伸手。那时候,不止是百姓们受不了,也会耽误朝廷的大事。

宋哲宗像
梁焘不反对“呼数十大姓计之,一日而足”,傅尧俞也不反对“借大姓李氏钱二十余万贯”,是因为北宋的赋役制度在设计上本就特别针对富户。用傅尧俞的话说就是:“乡村以人丁出力,城郭以等第出财,谓之差科”——乡村百姓主要负责给北宋朝廷提供人力,城市居民主要负责给朝廷提供钱财。不管是乡村百姓还是城市居民,谁的家产越多,谁就要承担更重的劳役和税赋。
当时在乡村推行的“衙前差役”便是如此。所谓“衙前差役”,其实质是官府将那些需要消耗人力、物力的政务直接摊派给百姓。被摊派到的百姓没有任何收入,但需承担许多工作。比如:
(1)押送漕粮。也就是从地方将粮食运往开封。开封城每年需要消耗粮食五六百万石,对衙前百姓来说这是最沉重的一项负担。
(2)搬运盐席。北宋实行盐酒茶专卖,衙前们必须负责给官府运盐,搬运多少按该衙前有多少资产(叫做“家业钱”)来算,一般是拥有一贯家产便须搬运两席盐(两席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50公斤)。如果一名被摊派了衙前的百姓被官府认定有两百贯家产,那他就得负责给官府搬运30吨盐。至于搬运到哪里,只能是官府说了算,这当中的成本全部由百姓自行负责,要是搬运过程中淋了雨受了潮,出现了损失,还得包赔。所以包拯当年上奏宋仁宗批评说,陕西百姓被衙前差役害苦了,许多人“虽家业已竭,而盐数未足”,把家产都花光了,也没能完成官府摊派的运盐任务。
(3)送纳钱物,追捕盗贼。要替官府运输赋税到指定仓库,或搬运各类货物到京城与边地军营。这也是极为痛苦的差事。其中最可怕的是官府会从中牟利,行贿到位的百姓会被指派距离较近、路途较平坦的目的地,否则就有破产亡家的风险。此外还要协助官府维持地方治安。
(4)管理仓库、场务与官庄。要负责仓库的收与出,必须对得上账,还得管好仓库里的物资,不能受潮损坏,否则就要用自己的家产来赔。要负责场务(比如冶铁场)的经营,保证给官府缴纳足够的税赋,每处场务都制定有税额考核标准,达不到就得拿自己的家产来补。要负责经营官田(朝廷是最大的土地主),保证官府的租粮收入,不够的部分也得拿家产来补。
(5)采购物品,主持驿站招待所。官府需要的物资,比如牛羊、生铁、木材、绸缎等,会交给承担衙前差役的百姓去各地采买。招待来往官员是地方政府的一笔大开支,这笔开支也会被摊派给百姓。
衙前差役没有明确的工作边界,以上只是较常见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有个人所得税与资产税等,收入越高税率往往也越高,是控制社会贫富分化、维持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北宋的衙前差役专门摊派给富户,看似也是如此,实则不然。首先,评定富户的标准掌握在官府手里,朝廷虽然定有资产标准,但各地请况不同,不会严格执行朝廷的标准,且地方上在执行时,为了将尽可能多的百姓纳入到可摊派群体,会尽可能多地去计算百姓的家产,时人形容官府的做法是一根笤帚、一条破板凳都要按市场最高价算成资产。其次,被评定为拥有摊派资格的富户后,具体会被摊派到什么样的工作,需要花费多少人力与物力,也没有固定标准,完全由官府说了算。不受约束的官府自然会尽最大可能转移行政成本并从中获利。
于是,最后的结果就是百姓们不敢努力致富,宁愿去做穷人。用司马光上奏宋英宗的话来说就是:“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衣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自从本朝在乡村推行了衙前差役,百姓们就陷入到了困乏的境地,他们不敢努力经营,因为做富人反不如做穷人,做富人会被摊派衙前差役,搞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穷人当然也绝不肯求富。多种一棵桑树,多养一头牛,就会被左邻右舍视为富户,就会被官府摊派衙前差役。这些都不敢做,自然更不敢去增加田产、修葺房舍了。总之就是赋役政策对富人太不友好,于是众人都积极地保持贫穷状态。

宋徽宗《瑞鹤图》中的开封城宣德门
北宋富户的噩梦,除了衙前差役,还有各种“科配”。衙前对乡村富户的伤害最大,科配对城市富户的伤害最大。
所谓“科配”,字面意思就是强制摊派,既包括强制分摊购买,也包括强制分摊出售,还包括强制分摊出钱。制度化的科配,主要是在城市富户中实施。用北宋官员刘挚的话说就是:“坊郭十等户自来已是承应官中配买之物,及饥馑、盗贼、河防、城垒缓急科率,郡县赖之”——按资产分为十等的城市居民,天然就应该承担官府的各种配买任务,有饥荒了,出盗贼了,河堤决口了,城池需要修缮了,城市居民都得摊派,或者出钱,或者出物资。这种科配没有固定标准,不是说你月收入达到了多少,然后就按确定的税率纳所得税;也不是说你有多少资产,然后就按固定税率纳资产税,而是由官府随机确定数额,用宋哲宗时代官员孙升的话说,就是“科率有名而无常数”——科配有固定的名目,但没有固定的数额。
有固定名目的科配,主要是由城市里的“行户”来承担。
所谓“行户”就是加入了由官府控制的行会的商户。在北宋时代的开封、杭州这类城市经商,哪怕只是如武大郎那般挑担卖炊饼,都必须加入官府控制的行会,否则便不允许经营。官府控制行会的目的,一是方便征税,二是方便科配——皇宫需要什么商品了,衙门需要什么商品了,或者是需要制作什么物品了,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行户,将任务摊派在他们头上。这种摊派基本是没利润可赚的赔本生意,所以行户们都很害怕。如果是官府有手工业方面的需求摊派下来(比如木匠活),那行会内部就会搞人人有份,谁也别想跑,想跑想躲避的会被同行举报。如果是涉及到商品买卖和直接出钱的摊派,官府会根据行户的资产等级进行分配,谁的资产越多,要承担的科配就越重。资产的认定由官府说了算,科配的额度也由官府说了算,自然会经常出现所谓的“富户”承担不起摊派的事请。宋神宗时,开封城的米商曹赟被摊派去替官府采购糯米五百石,因无力完成任务,只好上吊自杀。
此外,还有很多没有固定名目的临时新科配。
比如庆历元年(1041),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上奏宋仁宗说,他途径邠州、乾州、泾州、渭州等地,“所至人户,经臣有状称为不任科率,乞行减放。内潘原县郭下丝绢行人十余家,每家配借钱七十贯文,哀诉求免。”——这些州县的百姓都因北宋与西夏的战事而遭到了临时新科配,很多人给韩琦递状子说实在承受不住了,乞求减轻一点。其中潘原县城中有十余户丝绢行的百姓,每一户都被朝廷摊派了七十贯的借钱额度,他们拿不出这笔钱借给朝廷,只好哀求韩琦希望免掉。韩琦对宋仁宗说,他知道朝廷没钱,不想给朝廷添麻烦,所以没答应这些百姓的诉求,只希望朝廷抓紧时机讨贼,不要因为朝中有不同意见而把战事一年两年不断拖下去,那样的话经济状况会更糟糕。
韩琦的奏折其实提供了另一个信息:宋仁宗当年不止向开封城内的“数十大姓”借钱数十万贯,也不止向“大姓李氏”借钱二十余万贯,还曾向很底层的普通百姓借钱。潘原县在今天的甘肃平凉一带,在北宋时代已属于相当贫困的地区,该县“每家配借钱七十贯文”(配借意思就是强制出借)的那些丝绢业人士,大概已是该县比较富有之人。
这七十贯钱宋仁宗有没有还?笔者找不到直接的材料来说明。从“大姓李氏”的二十余万贯钱最后被赖账来推测,潘原县的小民们大概率也没拿到宋仁宗的还款。对这些小民们来说,那七十贯钱的重要新,其实远大于李氏的二十万贯。没有了二十万贯,李氏还是大姓。没有了七十贯,潘原县的小民们也许就要去讨饭。
(来源:腾讯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