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自:学习时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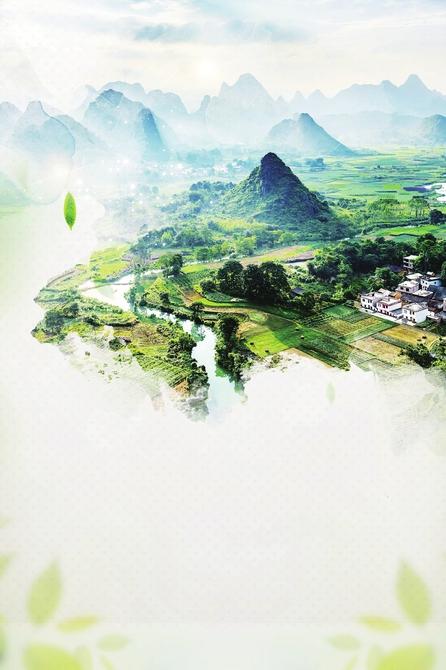
十二岁就去县城念书,寒暑假才回趟家;然后考学,谋生,少有回家;在上班的乡场安了家,回老家就更少了;随后,迁到了县城,再调到了重庆的市区。人越来越老,家越来越远。渐渐地,老家生疏了。偶尔回去一次,小道变宽了,高速路铺在农田上,老相识们还在村里的不多了,小年轻们就成陌生人,更分不出哪个娃是张家的,哪个妹是李家的。
即使很久不归,村前那条小河还是时常流进梦里,河边的老黄葛树似乎还会拂来轻风,掀起我稀疏的白发,或摇醒我的记忆。
最不能抹去的,是那连绵不绝的葱茏。一棵连着一棵的黄葛树,从我家门前出发,沿着河水流动的方向,一直铺延到老家的集市。
这些树啥时候种的?一个月朗星稀的夏夜,我和爷爷在树下乘凉,我问爷爷。爷爷说,它们可老了,比爷爷的爷爷还老!大约是几百年前,清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这里来了福建、湖南、广东、江西的客家人,他们很会做生意,从自贡买来盐,经真武码头贩运到贵州,再从贵州贩卖山货回来,生意越做越好。他们就在这新家园建房、安居下来,还在家门前、河边上都种上了黄葛树。真武这个小地方在随后的岁月里变了容貌。一棵棵客家人眼中的“思乡树”历经风雨长高长壮,一个个移民会馆占据了街市的要道,一串串真武故事开始在綦江河两岸流传……
过往的岁月,连老街上最老的大爷都说不完整了,恐怕只有那些苍老的树记进了年轮里。
我看到过黄葛树的年轮。有一天一晚惊雷,连着大吼的风,然后是哗哗的暴雨,吓得我缩在爷爷的怀里,很晚才蒙眬睡去。天亮了,雷雨总算闹腾够了停歇下来。可雨后一片凄凉,往日看似刚毅的树东倒西歪着,像扭伤了腰背。油房门口的那棵老黄葛树,被拦腰劈断。大人们开始收拾“残局”、清理道路,用长锯子把断裂的树桩截下来拖走。我看见那树桩的齐根处,是一圈圈的圆纹,像石子丢进小河,然后荡开。爷爷说,那是年轮,一岁一圈,记忆着黄葛树的年龄。
我小时候,綦江河畔已建了农场。锦橙、五月红、长叶橙……成片成片的柑橘树加入黄葛树的队列。天热了,有工人挑水抗旱;草多了,三天两头就被除掉,还有修枝、施肥、疏果,被侍弄得经心。黄葛树虽然无人看管、打理,却依然蓬勃生长,叶更密、杆更壮。
后来,农场又引进了新品种温州蜜橘。皮是青皮,肉却红嫩,味道确实好。试种之后要扩大规模,新林子需要修一条拖拉机能通往的路,有不少黄葛树恰好伫立其间,不得不请它让出道。那时节,黄葛芽正生发得旺盛,一天一抹鲜嫩的绿,清香四散,煞是好看、煞是好闻。它们好多被移栽去了远方,像我一样,别了小河,离开故土。
有一天,父亲从家乡传来喜讯:真武场口的河面上架设了大桥。于是,我专门回了趟老家,去河岸看新桥和久别的老树。平静的河面,横跨一道彩虹,身影曼妙;沿着河岸漫步,河边那排剩下的老黄葛树仍生生不息,聚拢团团浓荫,枝条伸到河心,黄叶飘飘洒洒,很美的景象。一条宽敞的河岸大道,将一个个树影连接,牵出长线,伸向远方。没了渡船的河边码头,虽然不再有从前的喧嚣、热闹,但是宁静、淡泊,一派安然。我倚着一棵粗壮的老树,看叶间簌簌落下的阳光,正映照着一块方正的铁牌,上面写着:“百年古树,注意保护。”这条小河,这些老树,还会相依相伴!
我知道我越来越留恋它们的原因。不管离家多少年,那条小河,小河边的老黄葛树,是我永远熟悉的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