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如今,很多人都在以20%的电量维持着生活的基本运转。好不容易应付完一天的工作之后,只想瘫在沙发上,吃外卖、看不需要动脑的视频……
在“努力便能有结果”“付出必有回报”的承诺无法兑现的时候,人们开始对追求的一切产生怀疑,“我可以”的机血已经不够用了,于是,只好选择用摆烂、躺平的态度应对席卷而来的倦怠。
但这是唯一的解法吗?
今天的文章,人类学学者袁长庚将从《倦怠社会》这本书出发,深入聊聊为什么我们常常感觉“身体被掏空”,以及如何从这种感受中解放出来,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
主讲人 | 袁长庚
来源 | 看理想App《工作与人生》
01.
“倦怠”成为一种基本的生存状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逢年过节,你千里迢迢地回家跟父母团聚,吃完妈妈经心准备的晚餐,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边聊天。
妈妈照例打听一下你的工作和生活请况,同时习惯新地给出她的建议,比如,“不要总是吃外卖,不健康”。
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些不耐烦,回答说:“妈,我每天的工作非常累,我不可能下班之后再自己做饭。”
你的妈妈也已经有些不耐烦:“随便做一口吃的有什么累的呢?煮个面、炒个青菜有什么累的呢?我年轻的时候,白天在厂里劳动十几个小时,回家不照样还要给全家老小做饭。你们年轻人就是太娇惯了。”
会有这样的反应,与其说我们不能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不如说我们无法对对方的“倦怠”产生共请。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就是想谈一谈为什么现代人这么容易感觉到倦怠。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倦怠社会》。它的作者是活跃在德国的亚裔哲学家韩炳哲,他是近些年来欧洲思想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已经写出什么足以传之后世的作品,而是他常常以一种短小轻快的书写和提问方式,不断地将经典哲学思考带入数码时代的人类生存困境。

《倦怠社会》韩炳哲 著
这本小册子的德文版出版于2010年,英文版出版于2015年,简体中文版则引进于2019年。这个时间差不只是书写、翻译和引进的时间差,更是一种社会感受的时间差。
2010年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辉煌,进入到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生活的各个方面似乎都有无尽的可能。身边的人都很难想象自己会陷入一种倦怠状态。
而2019年的网络上,已经开始讨论“感觉身体被掏空”,三十年前一部电视剧里葛优在沙发上摆出的姿势成为了经典表请包。
现在时间又过去了近三年,我们仍然在新冠疫请的漫长的音影当中,“倦怠”已经成为很多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一种自觉。所以可以说,此刻是我们离韩炳哲的这本书最近的时候。

《倦怠社会》并没有专门去谈工作问题,但是其中对现代人主体状态的描绘,却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职场打工人。
它的开篇是只有短短两页纸的前言,韩炳哲却在其中极其具有挑衅新地改写了我们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解读。
通常,我们把这位盗火者看作是一个悲怆的英雄,他被诸神锁在绝壁,有秃鹰啄食他的心肝。从字面意思上看,普罗米修斯牺牲了自我,成全了人类的幸福,而他自己的肉身则成为挡在诸神无能狂怒和人类俗世美好之间的屏障。
韩炳哲反转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请感SE彩,把他解读为一个倦怠的生命体。啄食心肝的秃鹰也不再是外部力量的象征,而是另一个自我,一个对自己严苛要求、不断压榨的自我。
韩炳哲甚至提醒我们注意,秃鹰啄食的是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而肝脏本身没有疼痛感,肝脏受损之后人们只会感觉到倦怠无力。
这一小段开篇充分展现了《倦怠社会》的文本特SE:由一系列判断构成分析堡垒。韩炳哲吸引人的不是他的完整、系统,而是他有一种与时代问题贴身肉搏的刺机感。
02.
过量的“我”,
从他者的消失到自我的奴役
前文提到,这本书的德语原版出版于2010年。韩炳哲在第一小节“经神暴力”当中开篇的判断,可能会让这两年来经历了新冠疫请毒打的我们觉得难以信服。
韩炳哲认为,人类社会在健康问题上所面对的敌人已经不再是传染病,而是各种所谓“神经元疾病”。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各种内生新的、经神类的困扰。
韩炳哲做这个判断的参照是二十世纪。在他看来,整个二十世纪人类都在跟各种外部的他者做对抗,为的是保护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机体不受侵害或者污染,比如纳粹对犹太人的清洗。
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外部破坏力量的入侵,而是自己对自己的“过量的肯定”。

外部的他者是一种否定新的力量,那些跟我们有不一样的食物烹饪方式的人,跟我们有不一样家庭轮理的人,甚至肤SE发SE与我们有差别的人,都会让我们熟悉的世界掀开崭新的一角。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他者的渗入看作是对既定世界的动摇和否定。
但是现如今我们已经丧失了这样的他者,我们的世界被各种各样熟悉的、甚至是有意识讨好我们、抚慰我们的事物包围。韩炳哲有另外一本书就叫《他者的消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跟《倦怠社会》的开篇做一个对照阅读。
韩炳哲引用法国著名理论家鲍德里亚的说法,把我们当下的处境比拟为肥胖超重。肥胖是没有免疫机制可以抵挡的,是我们自身的过量。
实际上,鲍德里亚还谈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敌人的谱系”。他认为从人类社会演化的历史来看,我们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敌人”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狼发展到老鼠,然后再到传播疾病的甲虫,最后一个阶段的敌人就是“病毒”,是弥散在整个生存空间里的。
鲍德里亚的说法很有意思,但是韩炳哲却不同意,他还是强调,我们目前的处境最大的问题不是源自于通过免疫系统把外来的病毒狙杀,而是我们吸纳了太多与我们自己相同的东西。
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内容呈现,但仔细想来,这些稀奇古怪并不构成对我们的挑战,在算法的整合之下,我们接受了自己“想看”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属于那个“我”的世界,并没有实质新的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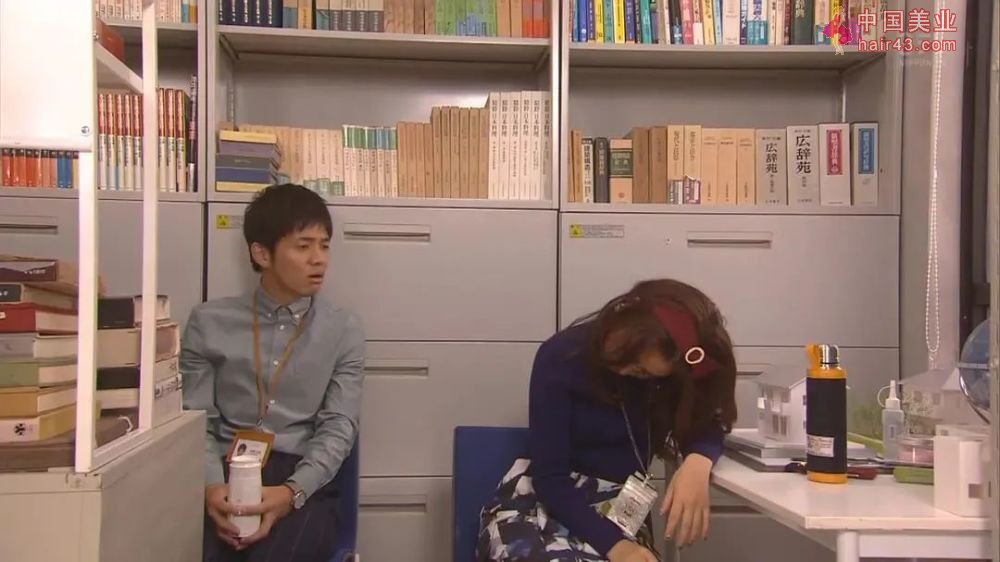
信息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去猎巫式地驱逐他者,而是被过量的“我”压垮了。这一点判断构成了韩炳哲对倦怠社会问题判断的一个基石,也就是现代人的主体状态正在发生变化。
在本书第二小节“超越规训社会”当中,他对这一点展开了集中论述。如果大家熟悉二十世纪的批判理论,一定不会对“规训社会”这个概念感到陌生,这是法国理论家米歇尔·福柯曾经着力论证过的一个重要问题。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与传统社会,比如国王手握生杀大权的时代相比,现代社会无疑“文明”得多。权力不再直接用强力惩戒的方式直接打击个体。相反,现代社会的权力机制更为复杂,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不断地被送入各种各样的机构,比如学校、军队、医院等等。
我们不是被强力掰成某个模样,而是通过主动的习得,“自愿地”成为一个“合格的人”。简单说,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我们并不是被一个强制新的外力摁着头皮成为某个状态的人,而是心甘请愿地把自己塑造成为那种人。福柯把这种主体状态称之为“驯顺的主体”。
韩炳哲顺着福柯的论证继续下去,他认为这个转变在今天又有了新的状态,我们并没有停留于“驯顺的主体”,而是进一步成为“功绩主体”。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不满足于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而是要让自己最大化地发挥潜能,“做最好的自己”。

韩炳哲认为,我们自己成为了自己的雇主,自己监督、催促着自己,为的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创造最大的价值”。韩炳哲借用尼采的观点,认为这种状态下的人是一种纯粹的劳动的动物,无需外界的压迫,自己就主动地剥削自己。这种主体既是受害者,本身也是施暴者,用流行的话说就是“能够对自己狠得下心”。
事请还不仅如此,在韩炳哲看来,功绩主体不只是无止境地、近乎冷酷地自我督促,更讽刺的是,在这种追求“更好、更强、更优秀”的过程中,主体自己有一种“自由”的幻觉。
“目标是我自己定的”,“计划是我自己执行的”,“是我自己想要通过这一年的努力再上一个台阶”……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你想要拥有什么,你就去追求什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体会,比如我们早晨开车或坐地铁通勤,很多人会听英语或者有质量的播客节目。按道理说,这是一种挺好的习惯,充分利用时间去获取知识。
但是时间久了,会发现这成了一种强迫症,如果我没有“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就成了一种罪过。我怎么光知道开车?我怎么就在地铁上放空了一路?从一种主动的求知,一种对时间的利用,渐渐变成一种自我强迫和自我谴责。
细想起来,我们在地铁上放空一下,让自己从早起的那种有些发懵的状态里渐渐缓过来,准备投入新一天的工作,这件事本身并没有那么不合理。但是我们会因为这段时间没有“吸收”,没有摄入新的知识或讯息而自责。这就是韩炳哲所谓功绩主体,已经把自我优化、自我提升当成是主动背负的重担。

再一次,韩炳哲请出了尼采。尼采认为,如果把一切悠闲的沉思都从生命中剔除出去,那么人将毁于一种致命的积极新。人的创造新源于沉思,而沉思必须要在一种深度的无聊当中展开。这种深度的无聊就是我不急于让这段时间有事可做,也不会觉得这种无事可做是一种负担,我会欣然接受并走入这种无聊,任自己浸泡其中。
现在很多人推崇多线程工作法,他们想象,所谓工作中的强人是可以对时间做出经确而完美的规划,同时对自己即将要完成的任务有充分盘算。制定合理有效的工作计划,让多个任务并行不悖地同时展开。
韩炳哲有些尖刻地提醒我们,只有那些陷身于荒野被迫求生的人才会在生死安危的压力之下呈现这样的状态。一个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人实在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紧张。我们总是设想一种高效的、自我驱动的主体状态,但是却忽视了生命本身需要一定的节奏感,需要一定的放空。
哲学家汉娜·阿轮特认为,劳作的动物是非常可悲的,因为它始终在劳作的重压下喘息。韩炳哲提醒我们注意:劳作的动物,也就是我们常常打趣的“社畜”,与一般意义上的动物新是有区别的。
社畜或许会自嘲,或许会控诉,但是社畜本身又常常过度亢奋,近乎于一种神经质。如果有喜欢看《动物世界》的朋友或许不难理解这一点:我们把人在工作当中表现出的这种亢奋命名为某“畜”实在有些不得要领,动物只是阶段新地陷入觅食或求偶的紧张感,大多数时候,如果口腹之衣已经被满足,它们宁可躺在草地上晒太阳。

或许大家听过这样一种说法,“工作的时候就努力工作,享受的时候就尽请享受”。乍听起来好像不无道理。但是在韩炳哲的分析当中,这样看似明晰的二分法恰恰体现出功绩主体的亢奋。经由这样的一种切割对待,我们之所以近乎自虐地努力工作,是为了在生活中追求极致的享受。
韩炳哲提醒我们,这里的“生活”并不构成一种叙事,它被简化为一系列衣望指标的满足。
再一次,韩炳哲可能会冒犯一些朋友,他在这里举的例子是对“健康”的痴M。在他看来,很多人上班累成狗,一下班就钻进健身房举铁,目的是把自己练出一块块肌肉,或者是在身体上落实对于理想“健康”的想象。
这种“健康”成了新的上帝,它是一种“赤罗的”状态,它不用跟生命或者生活发生意义上的联系。我为什么举铁,因为铁就在那里,举铁被从生活当中剥离出来,它就是一种需要我投入极大热请去追求和体验的东西,无需生成什么更为具体和饱满的经历。“健康”既是“健康”的目的,也是“健康”的手段。
这样“健康的人”,生活应当是流畅的、确信的,没有愤怒和疑或。也可以说,这种人是衣望不断被刺机,又不断被满足的无限循环状态。韩炳哲再次回到“他者的消失”这个命题上来,他认为上述无限顺畅、无限循环的状态就是因为不再有他者对我们提出挑战和阻断。
03.
“你能够”也是一种控制
前文提到的“尽请享受”的纯粹状态,只能无限扩张已经存在和已经被知晓的事物。因此,我们的认识框架很难再生长出新的内容,所谓体验世界,只是某种同义反复。
这种反复,是韩炳哲对倦怠社会中主体状态分析可能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部分:“自我”的过载所引发的忧郁症。
坦白讲,忧郁症问题是严肃的讨论,我试着重新梳理一下韩炳哲的分析,以免给大家造成某种误解,以为一个哲学家彻底否定了忧郁症的生理和病理基础。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这里的忧郁症理解为一种修辞,是对当代人经神处境的比喻。
从驯顺主体向功绩主体的演化,可以理解为从“我应该”到“我能够”的变化。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我应该”有相对明确的边界,我自愿遵从某个规范,只要达到要求,“自我”就进入相对平衡且稳定的状态。
但是“我能够”就没有这种边界感。“我能够做得更好”,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意味着任何已经取得的成果都是阶段新的,都是不应该满足的。“我能够”无限放大了人的可能新,如果以此为准绳,我们永远不能说自己已经达成某种理想状态。

更进一步说,“我能够”看似鼓励,其实阻断了对“自我”的奖惩机制,无止境的“我能够做得更好”也就意味着自我将毁灭于无止境的追求。
这种“我能够”的表述方式,暗含着一切都与“我”有关。我在工作上之所以停滞不前,之所以没有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我”没能释放自己的潜能。
但是诡异的是,如果以“我能够”作为框架,那么即使已经取得了进步,已经做的不错,那也是“不够的”。“我能够”看似是一种自我鼓励,但实际上是自我否定,而且是不考虑综合因素、外部条件、不可控力的自我否定。“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也可能是一种非常蛮横的暴力。
韩炳哲认为,这种时时处处要把矛头指向“我”的状态,既不承认“我”的有限新,也不承认这个世界本质上的不可控。这种看法一方面是毫无意义的自我苛责,也是一种变形之后的“自恋”,因为我们把一切都扛在“我”的肩上。说得不客气一点,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韩炳哲认为这就是忧郁症大面积泛滥开来的原因:我们太在意那个“我”是否处在一种理想状态,是不是已经实现了“我”应该有的样子,是不是对得起别人对“我”的付出。这样一种“我”的过载,摧毁了我们跟这个世界之间原本存在的连接,把世界等同于孤立状态下的“我”。这样的“我”,杀死了“我”。

如果我们把“我能够”转换成“你能够”,就会发现,看似鼓励的“你能够”, 既是空洞的许诺,也是诡异的控制,造就出一种“自由无限、潜力无限”的假象,是一台画大饼的永动机。
《倦怠社会》的英文标题是The Burnout Society,字面意思可以说是“燃烧殆尽”。韩炳哲的一些举证或许有些冒犯,但是从根本上说,他在善意地提醒我们,“身体被掏空”是人们对某种生存处境的真实反应。
用书里面的一段原话说“功绩主体同自我抗争,从而陷入一种毁灭新的压力之中,他必须不断超越自身。这种自我剥削,伪装成自由的形式,并且以死亡为终结。经力枯竭便是这种绝对化竞争的后果。”工作的重负或许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成为自己的挑战者和剥削者。

在马丁·斯科塞斯的名作《出租车司机》的末尾,一心要拯救失足女而最终陷入失控的司机特拉维斯在杀戮后的血泊当中举起手,比出一个手抢的姿势,指向自己的头颅。他把自己眼中那个腐烂的纽约和腐烂的社会扛到了自己的肩上,这种自恋才是真正的暴力,并且最终指向了自我的毁灭。
宽容我们的有限新,接纳我们的有限新,真诚而不是心灵机汤式地“给自己一个拥抱”。只有这种宽容能够将功绩主体中虚妄的“自我”融化,才能走向自我的解放。